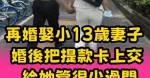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破籠完整後續

2/3
我親生父親的到來更是一下子讓他剩餘不多的生命燒到了底。
我生父姓徐,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,我媽從不肯提。
一日,徐生隻身潛入宋宅——宋宅門禁嚴,那時都以為他是找了什麼法子偷偷潛進來的,大喇喇地往沙發上一坐,張嘴就朝我媽要七位數。
我媽急得臉發白,拼了命地趕他,他不肯走,反而吃了喝,喝了睡,如同在自己家一般,賴了整整一天。
入夜,我放學回家,李世瑋也又來蹭晚飯。
徐生見到我,過來又是摸我臉,又是摸我頭,直感嘆不愧是他的兒子,長得真好。
我媽就尖聲叫著:「你做什麼!你做什麼!我都說了他不是你兒子!」
一邊將我護到身後,催促我回房。
宋秉誠那個時候已經很虛弱,輕易是不出房間的。他要靜,住在偏僻些的地方,那日不知怎麼,許是嗅到些不尋常的動靜,後來竟也拄著手杖出現在了客廳里。
那夜,由來都只嫌太空、空到一個人待著都有迴音的客廳里,填滿了哭聲、怒聲和吵鬧聲。我聽我媽的話回房間待了一會兒,卻怎麼都靜不下來,還是忍不住跑了出去。
等我再次跑進客廳,所有聲音都被無形的怪獸吞去了。靜悄悄。
廳里四人。
徐生趴在地上,臉朝下,後腦開花,鮮血仍有生命似的,向四處蔓延。
李世瑋腳邊是沾著血跡的花瓶碎片,他表情驚恐,連連後退,終於,劃破寂靜:「我沒殺人!我沒殺人!人不是我殺的!」
退至我媽身旁,他緊緊抓住我媽的手臂,「家姐,我都是為了你!你要想辦法!我不想坐牢,我不能去坐牢啊!!」
而我媽是靜止的。
從來哭聲最大、最愛大驚小怪的李真珠女士,是靜止的。
從頭到腳,她只有眼淚在動,只有眼淚在流。
更遠一些的沙發上,宋秉誠歪歪斜斜地仰躺著,眼睛不甘心,睜得好大,同樣已經斷了氣。
很久之後回憶那一晚,剝離出那些茫然、驚愕、恐怖的情緒,我會覺得那像是命運將有關於我生命的真相高度濃縮,在我面前上演了一出極具衝突的舞台劇。
我被剝奪身份,我見到生父,我發現他面目可憎,我失去他,我又失去宋秉誠。
我來不及拒絕,來不及阻止,來不及參與,來不及體會,我已經從戲劇高潮,來到戲劇結局。
現在我知道,原來命運才無心為我策劃戲劇,我人生最爆炸的一夜,引線由宋少淵點燃。
宋少淵補完整件事的來龍去脈。
「那時候,你媽受了那個叫徐豐的人威脅,出了一筆錢,請道上的人去滅他的口,當時她求的人,是興盛會的華七爺。華七那邊,有我契爺安插進去的線人,是我在聯絡,他將此事告知於我,我就順便把這事告訴了徐豐。」
「他知道你媽一面騙他說在籌錢,一面買兇滅他的口,很生氣,他此前偷渡到國外打了很多年黑工,才剛剛回港城不久,在這邊沒有什麼人脈,想找人幫忙都沒有辦法,於是我主動提出,我可以直接把他送進宋家,讓他找李真珠當面對質。」
「之後的事,你就知道了。我期待的那場戲,我看見了。」
後來回去的路上,我始終在想宋少淵的話。
老實說,我心裡有些牴觸知道那些事。在他把所有話都說完之後,我對他說,你沒有必要把這些事情一五一十全告訴我。
宋少淵則語氣平淡,「既然提到了,就告訴你吧,也沒什麼。」
之後,他望過來,望定我,「而且宋文瑾,我需要提醒你,雖然我答應過我媽,不會報復李真珠,但她當年做的事讓我媽受到很大的侮辱,我很難過去。假如還有什麼能讓她過得不舒服的機會送到我面前,我很可能還是會忍不住利用。你不要對我抱有什麼幻想,這就是我們的關係。」
他說完這些,我明白了自己之前因何而牴觸。
我確實對他抱有幻想,確實幾乎忘記橫亘在我們之間的那些東西,我大概……太把這些日子裡發生的那些親吻,和床上的親密當真。
宋少淵才是把控著這段關係的人,他始終清醒,感覺到我的放肆,於是也要讓我保持清醒。
所以他告訴我,是他往我家裡放了那條大狼狗,是他催化了在那一夜發生的所有事。
他知道我會介懷,他無所謂。
是,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。
我們之間沒有對錯,只有永遠循環往復的虧欠與被虧欠。一切量化的行為都沒意義,愛與恨都是如此混沌、叫人心力交瘁的東西。
我意識到,我已可笑地跌入渦流之中,觸了暗礁。
痛覺最易使人清醒。
什麼幻想,不再有了。他的策略奏效了。
16
「家姐,你原諒我吧,我真的真的知道錯了!」
早晨起床,聽見樓下一陣哭聲,走到樓梯邊向下探看,才知是李世瑋跪倒在我媽腳邊,聲淚俱下。
「我怎麼可能不在意你?我都為你殺過人,坐過牢,你記得嗎?你知不知牢里的日子有多辛苦,可只要想到是為你,想到從此以後那個姓徐的都不能夠再威脅你,我就覺得好值得!」
「家姐,你真的不要我?你都說了,我們就是彼此在這世上的另一個自己啊!」
我冷眼,甚至想要冷笑。
當年李世瑋用花瓶砸死徐豐後被捕,我媽花了很大的價錢請律師、疏通關係,最終讓他得了個過失殺人的判決,坐了沒兩年牢,就提前出獄。
那時他是什麼態度,怨天怨地,怨我媽不夠盡心,才讓他遭受牢獄之苦。我媽對他本來就好,這件事過後,更是感激他、心疼他、愧疚於他,簡直都恨不得供著他了,結果又換來什麼?不還是算計和欺騙。
但很顯然,此時此刻,我媽已將那些不快統統忘記。李世瑋不過又受了點傷,說了一籮筐好聽的話,她就和他哭作一團。
「好了好了,」見我面色鐵青,我媽抹了抹淚,招呼我,「都是一家人,哪有隔夜的仇?阿瑾,你舅舅也是一時糊塗,現在他都知道錯了,你也別再揪著不放,難不成你非要我和自己弟弟老死不相往來?」
我氣得好一陣子都待在學校沒有回家。
再回家,是我媽生日。
李世瑋裝模作樣地下廚做了一桌子的菜,最後還變戲法似的不知從哪裡變出一個生日蛋糕。
一看見那蛋糕,我媽眼淚「唰」一下就掉下來。
「家姐,你還記不記得,」李世瑋笑盈盈地,「剛來港城那一年,你過生日,看中一家蛋糕店的蛋糕,在那個玻璃窗前面蹲了好久。那時身上沒錢,沒辦法買給你,我就趁有個客人把那蛋糕買走,拎在手上剛出店門的時候,衝上去從他手裡搶。結果我跑得太慢了,被人抓住狠狠打了一頓。」
「當然記得,」我媽含淚說,「你太傻了,一個蛋糕而已,吃不到就不吃了,幹什麼要去搶呢?那次你被打得好慘,我都以為你要被打死了……」
「吶,那個時候沒讓你吃成的蛋糕,現在補給你了。是我按照記憶里的樣子自己做的,可能有些出入,你別嫌棄。」
嗤,這麼多年,早不送晚不送,偏偏這個時候送,還不就是看準我媽心軟,以後好繼續朝她伸手要錢。
我在心裡翻個白眼,打斷他的煽情:「好啦好啦,一味追憶往昔有什麼意思,還是要多多放眼未來。媽,你快許願吧。」
我媽在燭光里閉上眼睛,李世瑋趁此機會,沖我陰鷙地笑了笑。
我總覺得他那個笑容有深意,果不其然,吃完飯,他把我叫到院子裡,嘴裡叼著根煙,從外套的內口袋中掏出一疊東西,往我身上一拍。
只瞥了一眼,我心跳就差點暫停。
是照片,我和宋少淵的照片,擁抱,親吻,甚至還有床照!
「怎麼樣啊,你舅舅我還是有些本事吧,」李世瑋笑得下流又陰險,「酒店房間這幾張我可是費了點功夫的,還好,最終拍到的東西還是夠精彩,值了!」
「難怪之前我找他,告訴他你不是他親弟弟的時候他一點都不意外,原來你們兩兄弟的關係這麼——
「活、色、生、香啊。」
我咬了咬牙,面無表情地說:「什麼意思,要錢是嗎?」
李世瑋打了個響指,「聰明!」
「你怎麼不去找宋少淵?我這裡能有幾個錢。」
「他我可是惹不起了,但你跟他關係這麼親,從他那裡騙點錢過來,應該很簡單吧?」
「你要多少。」
「三百萬。知道你要錢也不易,可以分期給的。」
我簡直要笑出聲。
上次找宋少淵還是五十萬,這一次直接就上七位數。
三百萬!
怎麼不直接去搶銀行!
「沒有。」我把照片塞回他懷裡,「這些照片你想怎麼貼怎麼貼,我無所謂,但是你自己要掂量掂量貼出去之後,惹到宋少淵的後果。」
狠盯著他,我一字一句強調:「他不、可、能放過你。」
李世瑋顯然沒想到我這麼不管不顧,愣了一下說:「我知道你們不是親兄弟,外面的人可不知道,到時所有人都以為你們親兄弟亂倫,你們一輩子在港城抬不起頭來!」
「好啊,但不管抬不抬得起頭,宋少淵弄死你總還是綽綽有餘。」
「你……!你還有點廉恥嗎!」李世瑋氣急,「也是,都躺在男人身下任人乾了,你能有什麼廉恥?」
「哈。」我冷笑出聲,「還真是不好意思啊,廉恥心這種東西,我們家的人有一個算一個,全、都、沒、有。」
「你別逼我!」
「你隨意。」
只要我不被他威脅到,他就沒辦法。
我料定他不敢去犯宋少淵忌諱。
「宋文瑾!」李世瑋見我要走,惡狠狠地捏住我的手臂,「都是一家人,你是不是一定要這樣?上次你已經害我被切了根小指!三百萬而已,宋少淵他錢多得是!你他媽的替他守什麼財?你是被他乾得爽了就真他媽犯賤把自己當他老婆嗎?」
我不耐煩地想甩開他,不想拉扯之中,竟讓他身上揣著的那些照片灑了一地。
「你們在聊什麼,進來吃水果——」
話音未落,我媽陡然失聲。
她站在廊下,明與暗的交界線上,半邊被光照亮的臉上,已血色盡褪。
「這是什麼?」
「媽——」
「這是什麼?!」
我媽快步走過來,一把將我推開,彎腰撿起地上的一張照片,整個人一震,繼而揪住我,歇斯底里地喊道:
「宋文瑾,我問你這是什麼?!」
頭頂搖搖欲墜的一片樹葉被她聲音震落。
悠悠地,慢慢地。
落在了她的頭頂。
17
我媽沖回屋內,隨手抓起一把水果刀後,又沖向車庫。我在她將車落鎖前一秒跳上車,人未坐定,車已橫衝直撞地開了出去。
發動機的轟鳴聲響得我心頭直跳。
我媽死死盯著前路,盯得發狠,眼珠都要鼓起來,好似前面就有與她深仇大恨的人物,她就要直直地撞上去。
我不敢刺激她情緒,輕聲道:「媽,你冷靜一些。」
我媽不理。抑或根本就沒聽見。
一路加速狂飆,直到路過金碧酒店,看見宋少淵在門口在門口送別客人,她將車急急一剎。
金碧酒店在和記名下,近來新開張,剪彩那日的照片登了報,那時我媽還好奇地問我,這酒店難道是宋少淵私產。
我想她就是衝著此處來的,不想十分地巧,當然,我說是不巧,宋少淵真的也在。
我媽奮力拉開車門,直衝向街對面,聽她喊了聲「宋少淵!」人群霎時騷動。
我晚到一步,我媽揣了一路的那把水果刀,已經深深地扎進宋少淵左肩。
「是我對不起你媽!是我對不起你!要報應就報應到我身上來!宋少淵!為什麼動我兒子!」
她面色猙獰扭曲,瘋狂地將刀拔出,帶出一蓬噴濺的血。
她還要捅第二刀。
這一次宋少淵及時抬手扼住了她的手腕。
血從他肩膀的血洞中湧出,流了半身,他表情變也未變。
「宋文瑾,」看向我,他冷冰冰地說道,「你最好給我一個解釋。」
我也很難過,不知事情怎麼就變成這樣。
「對不起,哥......」
「你還喊他哥!你還喊他哥!」我媽歇斯底里,「他不是你哥!他是個禽獸,我殺了他——」
「砰!」
場面很混亂,又見了血,馬仔中有人拔了槍。
等我反應過來,劇痛已經襲來。子彈穿過了我的手臂,而我媽被我護在身前,很快便暈了過去。
......
昏睡一夜,第二日醒來,我媽仍十分激動,口中喊著要去殺了宋少淵。
我好疲憊地攔住她,她情緒失控地將我一同掃射:
「如今你還護著他?他都對你做出這樣禽獸的事情!
「我早說過他這人可怕,讓你離他遠些,你不聽!現在他都把你吃干抹凈了,你還乖乖叫他哥!你跟他道什麼歉?我問你,你跟他道什麼歉?!
「你知不知同性戀是病!精神病!他就是個瘋子!變態!難道你要被他傳染了嗎?
「宋文瑾,你說話!你告訴我,你都是被他逼的……」
「不是。」
我媽的聲音戛然而止。
「他沒有逼我,是我主動去找他,是我主動在他面前脫衣服。」
「你——」
「對!我!」我媽暴怒的聲音剛起了調,我用更高的聲音蓋過她,「你以為你欠的那一大筆錢我是怎麼還上的,我找宋少淵幫忙,不需要代價的嗎?」
一聽這話,我媽白了臉。她失神地後退兩步,跌坐回床上,好一會兒,忽又暴起,將我揪至身前,恨聲道:「宋文瑾,你怎能這樣自甘墮落!我辛辛苦苦培養你,如今你卻為了換錢,去爬男人的床?」
「我是為我自己嗎?」我出奇地冷靜,冷靜到我自己都驚訝,「家中花銷那麼大,你有沒有想過要節省?李世瑋揮霍無度,你為什麼要無底線地縱容他?你扮闊太扮習慣,宋秉誠死後,你由奢入儉難,好,我成全你!那你又知不知上大學後,我手上那些閒錢都是哪來的?」
我垂眼看著眼前這個女人。
四十歲,風華仍在。一張美貌無雙的臉,最青春時把自己交付於一個比自己大二十歲的男人,儘管卑微一些,但除此之外,她好像就不知道別的活法。
是愛著她的。我們畢竟在別人的輕視中,厚顏無恥地相依為命著。
也是厭著她的。厭著她的貪婪,厭著她的淺薄,厭著她的盲目,也厭著她烙刻在我身上的一切。
難道我不像她嗎?
「媽,你沒聽別人講過嗎?你兒子是個吃女人軟飯的小白臉。你不會以為宋少淵就是我討好的第一個吧。」
我知道自己要說出惡毒的話了,冥冥之中,像有一股無形的力量,催逼著我把話說出來。我甚至說得極盡誇張:
「要是沒有別人養著我,我哪有那麼多錢裝少爺,哪有錢給你買新衫買珠寶,哄你開心?
「你敢說宋秉誠死以後你沒有從別的男人那裡撈過錢?你也是這樣做的,我從你身上學來這些本事很正常吧,最起碼我還沒有插足別人家庭——」
「啪!」
我媽氣得渾身發抖,一巴掌重重地甩在我臉上。
我偏過頭去,耳邊嗡嗡地響。
「啪!」
又一巴掌。
再一巴掌。
我媽一句話未說,面無表情地一下一下抽著我的耳光。
我也這麼受著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,她可以處置我,隨意處置我。哪怕她要我還她這身血肉,也是該的。
等到我一邊臉已經完全沒了知覺,唇邊血絲不斷,她終於停了手。
也終於說了話。
「宋文瑾,你以後還做這麼不要臉的事,我就死給你看。」
18
這次我媽說到做到。
夜裡,宋少淵來家裡找我。他往大哥大上打了個電話,我以為我媽已經睡下,就偷偷地出門找他。
前夜太忙亂了,他受了傷,我也受了傷,傷口才剛剛包紮好,又有和記的人匆匆找過醫院來,說是哪片工地上出了事,他趕著去處理,最後繃帶打結都是胡亂打的,根本來不及與我多說什麼。
昨晚的事,我還欠他一個交代。
躡手躡腳地來到院裡,看見宋少淵的車。剛準備加快腳步,忽然,聽見頭頂一個幽幽的聲音:「宋文瑾。」
轉身仰頭,看見我媽坐在二樓露台的欄杆上,屋頂上那輪月亮不知怎麼有那麼大,照得她整身都慘白慘白。
「你就非要見他是嗎?」
說完,她跳了下來。
......
救護車趕到的時候,我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自己渾身冰涼。腦袋空空,機械地引著救護車駛入,機械地回答醫護人員的問題,機械地跟著他們跑。
宋少淵不知什麼時候過來的,他拉住我的手臂說話,我都只看見他嘴巴在動,聽不清他說什麼。但他好像要陪我上救護車。
「別,不用了。」我拂開他的手。我媽會瘋。
後來宋少淵還是自己開車到醫院來了。
手術室旁的長椅,他在我身邊坐下。
我仰頭靠著身後的牆壁,正看著頭頂的白熾燈發獃。感覺到身旁有人,我遲鈍地轉過頭去。
「沒事的。」宋少淵難得溫柔,將我往他懷裡攬了攬。
我沒有動。我的關節都好像生鏽了,不會動,只是任他攬著,僵硬地在他懷裡。
我想到還沒給他解釋,就輕聲說:「我舅舅拍了我們兩個的照片,昨天他拿照片威脅我要錢,結果照片被我媽看見了,她就瘋了。」
「好。」宋少淵沒發表什麼評論,只說,「照片的事我會處理。」
我閉了閉眼,「對不起,我沒攔住我媽。」
宋少淵摸了摸我的頭髮。
「你的傷怎麼樣了?」
「沒什麼事,都不痛了,你呢?」
「我也沒事。」宋少淵低下頭,又摸了摸我的臉,「你的臉又是怎麼回事?她打你嗎?」
我沒回答,看著地面發了很久的呆。
好多東西一齊在我腦袋裡面翻滾著。想說的很多,又沒什麼可說,只覺得好多糾葛都無意義。我與宋少淵,是什麼情比金堅的有情人嗎?鬧到如今地步,也不知是為何。
好累了。
最終我問宋少淵:「哥,我陪你睡了這麼久,欠你的那些債,還清了嗎?」
宋少淵沉默。沉默好久,說:「還清了。」
「那就不再還了,好嗎?」
「......」
沒聽見他的回答,我從他懷中坐起身,「可以嗎?」
宋少淵看著我,突然冷冷地笑了一下:
「我還以為最後說『夠了』的人會是我,我一直在想,我該在什麼時候覺得,你真正地還夠了。」
我不明白他說這話的意思,不過很快,他就明確地給了我答案:
「可以。
「你自由了。」
宋少淵離開了。
我看著手術室上亮起的紅燈,過了很久,才意識到自己視野里的紅色早已變得一片模糊。
我低下了頭。
將臉深深地埋進雙手之中。
不久,手術結束,我媽被轉至病房。醫生說傷勢無大礙,但需好好修養。
第二日,我託人將大哥大還給宋少淵。這電話我從來也只拿來跟他聯繫,以後聯繫必定少了,也或者根本就無需再聯繫,這麼貴的東西,留在身邊好像沒什麼用。
之後我的生活一下子變得特別平靜。
就連李世瑋都很長一段時間沒再搞什麼事。
宋少淵那邊大概是找過他,照片什麼的,他也沒再提過。
奇怪,原來真會有許多事情發生了,卻如同從未發生。
我的這個家,仍像從前一樣。我、我媽、舅舅,即使每兩個人之間,都那樣激烈地鬧過一場,可到頭來,兜兜轉轉,我們還是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吃飯。喜歡不喜歡,介懷不介懷的,都不重要,只要沒有殘殺彼此,日子總是這麼過下去。
而宋少淵,確實再也沒有聯繫過。
港城太小,倒也有些不期然的偶遇。
只是又能怎樣呢?
笑眯眯地打招呼,喊一聲「哥」罷了。
19
轉眼一年的時間就過去,日曆一撕撕到年底。
近來李世瑋春風得意,又神神秘秘,說是跟人合夥做了筆不錯的生意,掙了點小錢,在我面前恨不得都用鼻孔說話。我講他別是在搞什麼違法犯罪的東西,當心哪天二進宮,樂極生了悲,我媽就狠狠拍我的頭。
「你舅舅肯做生意是好事,你別說風涼話。」
我撇嘴。江山易改,本性難移,總之我不看好他。
這日李世瑋又煩我,一張報紙伸到我眼前,狂抖,我以為他又要同我吹什麼經濟形勢,莫名其妙,看也不看,便用手撥開。
「看看,你以前的姘頭,這就有新歡了,嘖嘖,轟轟烈烈,還登上報紙哦。」
我抬了抬眼皮,見「黑社會少東」、「賭王小兒子」、「同性戀情」之類的字眼,不甚感興趣地把報紙揉成一團,丟了。
不就是宋少淵和澳城那個簡潼之間那點破事,花邊小報來來回回都寫一個月了,也沒見寫出什麼花來。拍的那些照片,無非就是兩人走得近些,最最曖昧的也就是簡潼說話時,宋少淵附耳過去聽,怎麼,如今狗仔都是這個水平嗎?
我譏諷地說:「這些遠不及舅舅你當年拍的我和宋少淵的照片勁爆,那些照片底片你留著嗎?你拿去給這些小報記者賣一賣,說不定能談個好價錢,比你現在做的那什麼破生意都掙得多。」
我媽端著果盤走進來,「什麼東西掙得多?」
我和李世瑋便都識趣地止戰,難得地異口同聲:「沒什麼,亂聊。」
不敢在她面前提宋少淵,更不敢在她面前提那些照片。
自從因照片的事大鬧一場,跳樓,又做過手術後,我媽的身體一直不太好,情緒也都時好時壞,不太穩定。
李世瑋講話難聽,但有些話說得不是沒道理。他說他們的媽媽,也就是我外婆,生前就有點精神上的問題,聽說這個病會遺傳,所以現在我們都不想無端端地刺激到我媽。
「哦。對了,阿瑾,」我媽坐下,手指捻起果盤裡的一顆車厘子,「你說有朋友在遊輪上開跨年 Party,約你一起,你還有哪個朋友那麼有錢?真是朋友嗎?」
「……」我有些無奈,「媽,這麼多年你教我積極社交,還不知我認識的有錢人多嗎?人家就是愛熱鬧,這才廣發邀請,我也是想維護好關係,不想駁了人家面子,你又想什麼?」
我媽幽幽說:「我想什麼,還不是怕你又被誰金屋藏嬌了。」
「……金屋藏嬌不是這麼用。」
「哈哈哈哈哈!」李世瑋嘲笑得很大聲,「我說阿瑾你是得小心些,你這麼靚仔,說不定真的就有人又想藏你啊,那些少爺小姐玩得都很花的,你——」
「你閉嘴!顧著你自己吧。」
......
我確實是把這個 Party 當作拓展人脈的渠道去的,我也不知有那麼巧,竟在 Party 上遇見了宋少淵和簡潼。
簡潼我不認識,但他是個名人,幾乎沒人不知道他是澳城賭王家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小兒子。
他應該只比宋少淵小個一兩歲,個子也很高,但長了張娃娃臉,眼睛大大圓圓的,笑起來唇邊一對酒窩,顯年紀小。
多認識個人總沒壞處。我拿了杯香檳,拉了個關係比較好的朋友,走上前去。
先從認識的人招呼起,我笑著喊了宋少淵一聲:「哥。」
然後才朝簡潼伸手,「簡少爺,你好,初次見面,我是宋文瑾。」
簡潼看起來很吃驚,和我握了手後,輕輕撞了撞宋少淵的肩膀,很親昵的動作,「都姓宋,少淵,這是你弟弟?」
宋少淵看了看我,看了看我身邊的人,才說:「嗯,是我弟弟。」
簡潼是個比較活躍的性格,又仔細看了看我,笑,「你們看起來不太像哦,不過該說是你們家基因好嗎?都是難得的帥哥。」
宋少淵沒有解釋,我們向來是不對解釋這個的。
於是我也只是沖簡潼笑了一下,「謝謝。」
之後簡潼問我年齡,我說我比我哥小六歲,簡潼就挑眉說:「那你比我小,你也該叫我一聲哥。」
我從善如流:「哥。」
宋少淵冷道:「讓你叫聲哥還真容易。」
我沖他眨眨眼睛,用開玩笑的口吻調劑著:「放心哥,就算在外面有很多哥哥,你也是我唯一的親哥。」
「……誰是你親哥。」
宋少淵轉身走了。
20
一整晚,簡潼和宋少淵可以說是形影不離。看得出來他對宋少淵確實有意,看在我是宋少淵弟弟的份上,便也熱情地同我閒聊。
只可惜我提供不了什麼有價值的信息給他。我同宋少淵之間,只有一籮筐的破事,一籮筐的恩怨。
夜了,我喝多了酒有些犯困,便離開了一樓甲板,往樓上的房間走。
三樓遇見阿龍,神色焦慮,在樓梯邊團團轉。
阿龍是宋少淵手底下的人,也是今夜 Party 的保鏢之一,我們認識。見到他這副模樣,我奇怪地問他:「出什麼事了嗎?」
阿龍幾次三番欲言又止,最後還是說:「我看見有人往淵哥的酒里落了藥,然後那群人起著哄讓簡少爺把他送回房間了,我......我不知道要不要去敲門看看情況。」
「萬一,我說萬一啊,他們兩個借這個機會就……那什麼,我是不是算多管閒事啊?」
「可我明明看見有人落了藥,又不管不問,淵哥知道以後會罵死我的。」
「......」
靠,我實在忍不住爆粗口,真他媽的有病!
哪有撮合別人靠下藥的?
這幫少爺玩得也太離譜了,根本是唯恐天下不亂吧!
我捏了捏拳頭,問了阿龍房號,衝到房間門口。
剛抬手想敲門,又頓住。
萬一萬一,萬一宋少淵其實很願意呢?
簡潼長得好,家世好,又對他痴心,和他簡直不要太合適。
簡潼肯定也很願意做他的解藥。
宋少淵喜歡男人,又是個正常男人,中了藥,身旁又有願意的人,好像沒什麼拒絕的道理。
我猶豫著,房裡忽然傳來很大的動靜。我心裡一瞬間酸得厲害,想走都邁不出步。
受不了!
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!
不知道也就罷了,知道了,站在門口了,我怎麼能忍住不敲這個門?
反正下藥也不是什麼光明磊落的事,今日我就偏管這個閒事!
不想了,我立刻屈起指節敲了幾下門。
「哥!」
「哥!」
「哥你還好嗎?」
沒得到回應,索性變成用力拍。
「宋少淵!宋少淵!」
「宋少淵你——」
門「轟」地一聲開了。
宋少淵站在門裡,上半身赤裸,渾身濕透,一雙眼睛血絲遍布,紅得不正常。
「你幹什麼?」他用很沙啞的聲音問我。
我聽見房間裡有奇怪的聲音,直接越過他往裡面走,震驚地發現簡潼衣衫不整——但被宋少淵用繩子綁起來了。
「阿瑾!」他掙扎著,「快幫我把繩子解開!」
我有些傻眼,走上前去給他解開繩結,他起身整理好自己的衣服,一揚手就給了宋少淵一拳。
簡潼臉通紅,眼睛裡含了點淚,說:「宋少淵,我從來沒有被人這麼羞辱過!」
「對不住,我也只是希望你冷靜點。」
「你這樣看不上我,我也沒必要再自作多情!」
簡潼怒氣沖沖地離開。
門關上後,我突然就尷尬起來,乾笑一聲,「你們兩個……到底誰中藥啊?」
「知道我中藥還主動送上門來?」
宋少淵用力將我摜在牆上。他的身體很燙,就連浸了水的褲子都散出一股熱氣。敲門時我沒考慮後果,此刻對上他那雙被慾望燒得通紅的眼睛,有些慌了。
我硬著頭皮問:「你、你還好嗎?」
宋少淵咬了咬牙,汗水從他的額頭中間滾下來,「你覺得呢?」
說完他把我狠狠往旁邊一推,「快滾!」
他逕自走進浴室,打開了花灑。我跟著走到門口,水珠噼里啪啦地飛濺,濺上我的臉,很涼。
無事發生,其實我是該走了。
但我看著他,就有什麼東西將我釘在原地。
「不走?」宋少淵在水簾中看我一眼,然後不再理會,背過身將自己濕漉漉的褲子脫下來,一個微妙的角度,我看見他的右手在做什麼。
他左手扶住了牆壁,指節微微曲著,手背上浮起青筋,一直延伸到他的小臂上去。
水順著他的頭髮、他的背脊、他精窄的腰身向下流,水聲里摻雜著模糊的喘息。
我走進去,關上了浴室門。
「咔嚓」一聲,使得宋少淵回頭。
我張了張嘴,「哥,我幫你。」
......
半浴缸的水,我在與宋少淵激烈的親吻中,推著他跌進去,自己瞬間也被浸透了。
我憋著一股力氣,抓住宋少淵飽滿的胸肌跨坐在他身上。宋少淵亦十分用力地掐著我的腰。
痛苦到極致是種快感,快感到極致便也是痛苦。深深地感覺到他時,我似乎是痛苦了。
人們總是很快地墜入愛河,很快地分開,相愛難道不是好簡單的一件事;或如簡潼一般,「你看不上我,我便不自作多情」,放手難道不是好簡單的一件事,為何我和宋少淵之間,就那樣複雜?
然而又慶幸於那點複雜。
曾經不甘於只喊一聲「哥」,如今卻想,至少至少,還可以叫一聲哥。
「哥。」
我呢喃著,吻住他。
這其實是我們最珍貴的聯結。
21
波濤浪涌整整一夜都未平息。
結束後我原本想撐著不閉眼,趁宋少淵睡去就先行離開,再做無事發生。誰知他竟是假寐。我剛一掀被,腰就被他手臂勒住,聽見他說:「睡覺。」
我被他強行按住躺了回去。
「不累嗎?有事睡醒再說,現在睡覺。」
本來也很倦了,我到底沒撐住,在他懷裡睡了過去。
醒來時已是下午,宋少淵不在房間。我穿好衣服下到一樓,看見宋少淵坐在沙發上,表情很冷。而他身前站著的那幾個年輕些的,都是平日裡行事張揚被人捧上天的大少爺,此刻,他們個個垂著頭,面上儘是宿醉後褪不去的疲倦,還有說不出的心虛和尷尬。
「淵哥,真的對不住,我們這不是以為你和潼哥……就差臨門一腳嗎。」
「我們有分寸的,就只往你杯里放了少少一點,真的,就只是助助興的程度!」
只是少少一點?
我懷疑。宋少淵明明一個晚上都很......
「怎麼?」宋少淵冷冷地抬起眼皮,「少少一點就不是給我下藥了?非要我慾火焚身暴斃而亡,你們才覺得自己闖了大禍?」
那幾人竟都有些怕他的樣子,聽他這麼說就著了慌,最後一絲殘存的困意都沒了,爭先恐後地圍上去道歉。
臨近傍晚時,Party 徹底散場,遊輪泊入碼頭。
下船後宋少淵把車開到我身邊。他沒帶司機,自己開的車。我見周圍不少人,扭扭捏捏也奇怪,就拉開副駕駛的車門上去了。
路上也沒說什麼。
我好奇問了他一句,那幾個下藥的你這麼說兩句就算完了?他聽完只一聲冷笑,我就懂了。
肯定是沒完。礙於各家面子他沒撕破臉,但後頭他總能找到辦法整他們。
「有哪裡不舒服嗎?」宋少淵突然問。
我沒想到他還提這個,抿了抿唇,說:「沒有。」
大轉彎,宋少淵專注地看著前路,手上轉著方向盤,聲音淡淡飄過來,「昨夜敲門那麼急,怕我跟簡潼亂性?」
我轉頭朝他看去,他恰巧也側過臉,視線相撞,他追逼:「嗯?」
我便說:「是阿龍說看見有人朝你杯里落藥,我又不知什麼藥……我還是會擔心你的,哥。」
宋少淵輕笑一聲,過了一會兒,才又說:「那算我欠你一次,畢竟你還是幫我很大的忙。」
天邊夕陽行將燒盡,汽車駛入繁華些的路段,馬路邊已有少數霓虹招牌亮起,各色燈光擠占視線。
港城總是這樣地繚亂。
我望著窗外飛逝而過的街景,忽而視線一定。
是......我媽?
她幾乎不來這樣的舊城區,怎還站在人潮湧動的街頭,與一個陌生的男人——
不,不對,不是陌生男人。
是李世瑋。
他做了些偽裝,但我們做了二十幾年的親人,他的身形我太熟悉。
我不禁想起前些天,我媽對我抱怨說,阿瑋好一陣子都無音信,也不來看她,不知是做什麼去了。
當時我未在意,畢竟我這個舅舅從前就如此,沉迷賭場或花天酒地,誰知他是不是又玩得忘記今夕何夕?
如今他又是在搞什麼神秘?
我忍不住叫宋少淵停了車,坐在車裡遠遠地觀察。
沒多久,兩人說完了話,我媽似乎不舍,抓住他的手好一會兒,李世瑋拍拍她,似是安撫,然後轉過身,壓低帽檐,匯入人流。
我生父姓徐,我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,我媽從不肯提。
一日,徐生隻身潛入宋宅——宋宅門禁嚴,那時都以為他是找了什麼法子偷偷潛進來的,大喇喇地往沙發上一坐,張嘴就朝我媽要七位數。
我媽急得臉發白,拼了命地趕他,他不肯走,反而吃了喝,喝了睡,如同在自己家一般,賴了整整一天。
入夜,我放學回家,李世瑋也又來蹭晚飯。
徐生見到我,過來又是摸我臉,又是摸我頭,直感嘆不愧是他的兒子,長得真好。
我媽就尖聲叫著:「你做什麼!你做什麼!我都說了他不是你兒子!」
一邊將我護到身後,催促我回房。
宋秉誠那個時候已經很虛弱,輕易是不出房間的。他要靜,住在偏僻些的地方,那日不知怎麼,許是嗅到些不尋常的動靜,後來竟也拄著手杖出現在了客廳里。
那夜,由來都只嫌太空、空到一個人待著都有迴音的客廳里,填滿了哭聲、怒聲和吵鬧聲。我聽我媽的話回房間待了一會兒,卻怎麼都靜不下來,還是忍不住跑了出去。
等我再次跑進客廳,所有聲音都被無形的怪獸吞去了。靜悄悄。
廳里四人。
徐生趴在地上,臉朝下,後腦開花,鮮血仍有生命似的,向四處蔓延。
李世瑋腳邊是沾著血跡的花瓶碎片,他表情驚恐,連連後退,終於,劃破寂靜:「我沒殺人!我沒殺人!人不是我殺的!」
退至我媽身旁,他緊緊抓住我媽的手臂,「家姐,我都是為了你!你要想辦法!我不想坐牢,我不能去坐牢啊!!」
而我媽是靜止的。
從來哭聲最大、最愛大驚小怪的李真珠女士,是靜止的。
從頭到腳,她只有眼淚在動,只有眼淚在流。
更遠一些的沙發上,宋秉誠歪歪斜斜地仰躺著,眼睛不甘心,睜得好大,同樣已經斷了氣。
很久之後回憶那一晚,剝離出那些茫然、驚愕、恐怖的情緒,我會覺得那像是命運將有關於我生命的真相高度濃縮,在我面前上演了一出極具衝突的舞台劇。
我被剝奪身份,我見到生父,我發現他面目可憎,我失去他,我又失去宋秉誠。
我來不及拒絕,來不及阻止,來不及參與,來不及體會,我已經從戲劇高潮,來到戲劇結局。
現在我知道,原來命運才無心為我策劃戲劇,我人生最爆炸的一夜,引線由宋少淵點燃。
宋少淵補完整件事的來龍去脈。
「那時候,你媽受了那個叫徐豐的人威脅,出了一筆錢,請道上的人去滅他的口,當時她求的人,是興盛會的華七爺。華七那邊,有我契爺安插進去的線人,是我在聯絡,他將此事告知於我,我就順便把這事告訴了徐豐。」
「他知道你媽一面騙他說在籌錢,一面買兇滅他的口,很生氣,他此前偷渡到國外打了很多年黑工,才剛剛回港城不久,在這邊沒有什麼人脈,想找人幫忙都沒有辦法,於是我主動提出,我可以直接把他送進宋家,讓他找李真珠當面對質。」
「之後的事,你就知道了。我期待的那場戲,我看見了。」
後來回去的路上,我始終在想宋少淵的話。
老實說,我心裡有些牴觸知道那些事。在他把所有話都說完之後,我對他說,你沒有必要把這些事情一五一十全告訴我。
宋少淵則語氣平淡,「既然提到了,就告訴你吧,也沒什麼。」
之後,他望過來,望定我,「而且宋文瑾,我需要提醒你,雖然我答應過我媽,不會報復李真珠,但她當年做的事讓我媽受到很大的侮辱,我很難過去。假如還有什麼能讓她過得不舒服的機會送到我面前,我很可能還是會忍不住利用。你不要對我抱有什麼幻想,這就是我們的關係。」
他說完這些,我明白了自己之前因何而牴觸。
我確實對他抱有幻想,確實幾乎忘記橫亘在我們之間的那些東西,我大概……太把這些日子裡發生的那些親吻,和床上的親密當真。
宋少淵才是把控著這段關係的人,他始終清醒,感覺到我的放肆,於是也要讓我保持清醒。
所以他告訴我,是他往我家裡放了那條大狼狗,是他催化了在那一夜發生的所有事。
他知道我會介懷,他無所謂。
是,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。
我們之間沒有對錯,只有永遠循環往復的虧欠與被虧欠。一切量化的行為都沒意義,愛與恨都是如此混沌、叫人心力交瘁的東西。
我意識到,我已可笑地跌入渦流之中,觸了暗礁。
痛覺最易使人清醒。
什麼幻想,不再有了。他的策略奏效了。
16
「家姐,你原諒我吧,我真的真的知道錯了!」
早晨起床,聽見樓下一陣哭聲,走到樓梯邊向下探看,才知是李世瑋跪倒在我媽腳邊,聲淚俱下。
「我怎麼可能不在意你?我都為你殺過人,坐過牢,你記得嗎?你知不知牢里的日子有多辛苦,可只要想到是為你,想到從此以後那個姓徐的都不能夠再威脅你,我就覺得好值得!」
「家姐,你真的不要我?你都說了,我們就是彼此在這世上的另一個自己啊!」
我冷眼,甚至想要冷笑。
當年李世瑋用花瓶砸死徐豐後被捕,我媽花了很大的價錢請律師、疏通關係,最終讓他得了個過失殺人的判決,坐了沒兩年牢,就提前出獄。
那時他是什麼態度,怨天怨地,怨我媽不夠盡心,才讓他遭受牢獄之苦。我媽對他本來就好,這件事過後,更是感激他、心疼他、愧疚於他,簡直都恨不得供著他了,結果又換來什麼?不還是算計和欺騙。
但很顯然,此時此刻,我媽已將那些不快統統忘記。李世瑋不過又受了點傷,說了一籮筐好聽的話,她就和他哭作一團。
「好了好了,」見我面色鐵青,我媽抹了抹淚,招呼我,「都是一家人,哪有隔夜的仇?阿瑾,你舅舅也是一時糊塗,現在他都知道錯了,你也別再揪著不放,難不成你非要我和自己弟弟老死不相往來?」
我氣得好一陣子都待在學校沒有回家。
再回家,是我媽生日。
李世瑋裝模作樣地下廚做了一桌子的菜,最後還變戲法似的不知從哪裡變出一個生日蛋糕。
一看見那蛋糕,我媽眼淚「唰」一下就掉下來。
「家姐,你還記不記得,」李世瑋笑盈盈地,「剛來港城那一年,你過生日,看中一家蛋糕店的蛋糕,在那個玻璃窗前面蹲了好久。那時身上沒錢,沒辦法買給你,我就趁有個客人把那蛋糕買走,拎在手上剛出店門的時候,衝上去從他手裡搶。結果我跑得太慢了,被人抓住狠狠打了一頓。」
「當然記得,」我媽含淚說,「你太傻了,一個蛋糕而已,吃不到就不吃了,幹什麼要去搶呢?那次你被打得好慘,我都以為你要被打死了……」
「吶,那個時候沒讓你吃成的蛋糕,現在補給你了。是我按照記憶里的樣子自己做的,可能有些出入,你別嫌棄。」
嗤,這麼多年,早不送晚不送,偏偏這個時候送,還不就是看準我媽心軟,以後好繼續朝她伸手要錢。
我在心裡翻個白眼,打斷他的煽情:「好啦好啦,一味追憶往昔有什麼意思,還是要多多放眼未來。媽,你快許願吧。」
我媽在燭光里閉上眼睛,李世瑋趁此機會,沖我陰鷙地笑了笑。
我總覺得他那個笑容有深意,果不其然,吃完飯,他把我叫到院子裡,嘴裡叼著根煙,從外套的內口袋中掏出一疊東西,往我身上一拍。
只瞥了一眼,我心跳就差點暫停。
是照片,我和宋少淵的照片,擁抱,親吻,甚至還有床照!
「怎麼樣啊,你舅舅我還是有些本事吧,」李世瑋笑得下流又陰險,「酒店房間這幾張我可是費了點功夫的,還好,最終拍到的東西還是夠精彩,值了!」
「難怪之前我找他,告訴他你不是他親弟弟的時候他一點都不意外,原來你們兩兄弟的關係這麼——
「活、色、生、香啊。」
我咬了咬牙,面無表情地說:「什麼意思,要錢是嗎?」
李世瑋打了個響指,「聰明!」
「你怎麼不去找宋少淵?我這裡能有幾個錢。」
「他我可是惹不起了,但你跟他關係這麼親,從他那裡騙點錢過來,應該很簡單吧?」
「你要多少。」
「三百萬。知道你要錢也不易,可以分期給的。」
我簡直要笑出聲。
上次找宋少淵還是五十萬,這一次直接就上七位數。
三百萬!
怎麼不直接去搶銀行!
「沒有。」我把照片塞回他懷裡,「這些照片你想怎麼貼怎麼貼,我無所謂,但是你自己要掂量掂量貼出去之後,惹到宋少淵的後果。」
狠盯著他,我一字一句強調:「他不、可、能放過你。」
李世瑋顯然沒想到我這麼不管不顧,愣了一下說:「我知道你們不是親兄弟,外面的人可不知道,到時所有人都以為你們親兄弟亂倫,你們一輩子在港城抬不起頭來!」
「好啊,但不管抬不抬得起頭,宋少淵弄死你總還是綽綽有餘。」
「你……!你還有點廉恥嗎!」李世瑋氣急,「也是,都躺在男人身下任人乾了,你能有什麼廉恥?」
「哈。」我冷笑出聲,「還真是不好意思啊,廉恥心這種東西,我們家的人有一個算一個,全、都、沒、有。」
「你別逼我!」
「你隨意。」
只要我不被他威脅到,他就沒辦法。
我料定他不敢去犯宋少淵忌諱。
「宋文瑾!」李世瑋見我要走,惡狠狠地捏住我的手臂,「都是一家人,你是不是一定要這樣?上次你已經害我被切了根小指!三百萬而已,宋少淵他錢多得是!你他媽的替他守什麼財?你是被他乾得爽了就真他媽犯賤把自己當他老婆嗎?」
我不耐煩地想甩開他,不想拉扯之中,竟讓他身上揣著的那些照片灑了一地。
「你們在聊什麼,進來吃水果——」
話音未落,我媽陡然失聲。
她站在廊下,明與暗的交界線上,半邊被光照亮的臉上,已血色盡褪。
「這是什麼?」
「媽——」
「這是什麼?!」
我媽快步走過來,一把將我推開,彎腰撿起地上的一張照片,整個人一震,繼而揪住我,歇斯底里地喊道:
「宋文瑾,我問你這是什麼?!」
頭頂搖搖欲墜的一片樹葉被她聲音震落。
悠悠地,慢慢地。
落在了她的頭頂。
17
我媽沖回屋內,隨手抓起一把水果刀後,又沖向車庫。我在她將車落鎖前一秒跳上車,人未坐定,車已橫衝直撞地開了出去。
發動機的轟鳴聲響得我心頭直跳。
我媽死死盯著前路,盯得發狠,眼珠都要鼓起來,好似前面就有與她深仇大恨的人物,她就要直直地撞上去。
我不敢刺激她情緒,輕聲道:「媽,你冷靜一些。」
我媽不理。抑或根本就沒聽見。
一路加速狂飆,直到路過金碧酒店,看見宋少淵在門口在門口送別客人,她將車急急一剎。
金碧酒店在和記名下,近來新開張,剪彩那日的照片登了報,那時我媽還好奇地問我,這酒店難道是宋少淵私產。
我想她就是衝著此處來的,不想十分地巧,當然,我說是不巧,宋少淵真的也在。
我媽奮力拉開車門,直衝向街對面,聽她喊了聲「宋少淵!」人群霎時騷動。
我晚到一步,我媽揣了一路的那把水果刀,已經深深地扎進宋少淵左肩。
「是我對不起你媽!是我對不起你!要報應就報應到我身上來!宋少淵!為什麼動我兒子!」
她面色猙獰扭曲,瘋狂地將刀拔出,帶出一蓬噴濺的血。
她還要捅第二刀。
這一次宋少淵及時抬手扼住了她的手腕。
血從他肩膀的血洞中湧出,流了半身,他表情變也未變。
「宋文瑾,」看向我,他冷冰冰地說道,「你最好給我一個解釋。」
我也很難過,不知事情怎麼就變成這樣。
「對不起,哥......」
「你還喊他哥!你還喊他哥!」我媽歇斯底里,「他不是你哥!他是個禽獸,我殺了他——」
「砰!」
場面很混亂,又見了血,馬仔中有人拔了槍。
等我反應過來,劇痛已經襲來。子彈穿過了我的手臂,而我媽被我護在身前,很快便暈了過去。
......
昏睡一夜,第二日醒來,我媽仍十分激動,口中喊著要去殺了宋少淵。
我好疲憊地攔住她,她情緒失控地將我一同掃射:
「如今你還護著他?他都對你做出這樣禽獸的事情!
「我早說過他這人可怕,讓你離他遠些,你不聽!現在他都把你吃干抹凈了,你還乖乖叫他哥!你跟他道什麼歉?我問你,你跟他道什麼歉?!
「你知不知同性戀是病!精神病!他就是個瘋子!變態!難道你要被他傳染了嗎?
「宋文瑾,你說話!你告訴我,你都是被他逼的……」
「不是。」
我媽的聲音戛然而止。
「他沒有逼我,是我主動去找他,是我主動在他面前脫衣服。」
「你——」
「對!我!」我媽暴怒的聲音剛起了調,我用更高的聲音蓋過她,「你以為你欠的那一大筆錢我是怎麼還上的,我找宋少淵幫忙,不需要代價的嗎?」
一聽這話,我媽白了臉。她失神地後退兩步,跌坐回床上,好一會兒,忽又暴起,將我揪至身前,恨聲道:「宋文瑾,你怎能這樣自甘墮落!我辛辛苦苦培養你,如今你卻為了換錢,去爬男人的床?」
「我是為我自己嗎?」我出奇地冷靜,冷靜到我自己都驚訝,「家中花銷那麼大,你有沒有想過要節省?李世瑋揮霍無度,你為什麼要無底線地縱容他?你扮闊太扮習慣,宋秉誠死後,你由奢入儉難,好,我成全你!那你又知不知上大學後,我手上那些閒錢都是哪來的?」
我垂眼看著眼前這個女人。
四十歲,風華仍在。一張美貌無雙的臉,最青春時把自己交付於一個比自己大二十歲的男人,儘管卑微一些,但除此之外,她好像就不知道別的活法。
是愛著她的。我們畢竟在別人的輕視中,厚顏無恥地相依為命著。
也是厭著她的。厭著她的貪婪,厭著她的淺薄,厭著她的盲目,也厭著她烙刻在我身上的一切。
難道我不像她嗎?
「媽,你沒聽別人講過嗎?你兒子是個吃女人軟飯的小白臉。你不會以為宋少淵就是我討好的第一個吧。」
我知道自己要說出惡毒的話了,冥冥之中,像有一股無形的力量,催逼著我把話說出來。我甚至說得極盡誇張:
「要是沒有別人養著我,我哪有那麼多錢裝少爺,哪有錢給你買新衫買珠寶,哄你開心?
「你敢說宋秉誠死以後你沒有從別的男人那裡撈過錢?你也是這樣做的,我從你身上學來這些本事很正常吧,最起碼我還沒有插足別人家庭——」
「啪!」
我媽氣得渾身發抖,一巴掌重重地甩在我臉上。
我偏過頭去,耳邊嗡嗡地響。
「啪!」
又一巴掌。
再一巴掌。
我媽一句話未說,面無表情地一下一下抽著我的耳光。
我也這麼受著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,她可以處置我,隨意處置我。哪怕她要我還她這身血肉,也是該的。
等到我一邊臉已經完全沒了知覺,唇邊血絲不斷,她終於停了手。
也終於說了話。
「宋文瑾,你以後還做這麼不要臉的事,我就死給你看。」
18
這次我媽說到做到。
夜裡,宋少淵來家裡找我。他往大哥大上打了個電話,我以為我媽已經睡下,就偷偷地出門找他。
前夜太忙亂了,他受了傷,我也受了傷,傷口才剛剛包紮好,又有和記的人匆匆找過醫院來,說是哪片工地上出了事,他趕著去處理,最後繃帶打結都是胡亂打的,根本來不及與我多說什麼。
昨晚的事,我還欠他一個交代。
躡手躡腳地來到院裡,看見宋少淵的車。剛準備加快腳步,忽然,聽見頭頂一個幽幽的聲音:「宋文瑾。」
轉身仰頭,看見我媽坐在二樓露台的欄杆上,屋頂上那輪月亮不知怎麼有那麼大,照得她整身都慘白慘白。
「你就非要見他是嗎?」
說完,她跳了下來。
......
救護車趕到的時候,我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自己渾身冰涼。腦袋空空,機械地引著救護車駛入,機械地回答醫護人員的問題,機械地跟著他們跑。
宋少淵不知什麼時候過來的,他拉住我的手臂說話,我都只看見他嘴巴在動,聽不清他說什麼。但他好像要陪我上救護車。
「別,不用了。」我拂開他的手。我媽會瘋。
後來宋少淵還是自己開車到醫院來了。
手術室旁的長椅,他在我身邊坐下。
我仰頭靠著身後的牆壁,正看著頭頂的白熾燈發獃。感覺到身旁有人,我遲鈍地轉過頭去。
「沒事的。」宋少淵難得溫柔,將我往他懷裡攬了攬。
我沒有動。我的關節都好像生鏽了,不會動,只是任他攬著,僵硬地在他懷裡。
我想到還沒給他解釋,就輕聲說:「我舅舅拍了我們兩個的照片,昨天他拿照片威脅我要錢,結果照片被我媽看見了,她就瘋了。」
「好。」宋少淵沒發表什麼評論,只說,「照片的事我會處理。」
我閉了閉眼,「對不起,我沒攔住我媽。」
宋少淵摸了摸我的頭髮。
「你的傷怎麼樣了?」
「沒什麼事,都不痛了,你呢?」
「我也沒事。」宋少淵低下頭,又摸了摸我的臉,「你的臉又是怎麼回事?她打你嗎?」
我沒回答,看著地面發了很久的呆。
好多東西一齊在我腦袋裡面翻滾著。想說的很多,又沒什麼可說,只覺得好多糾葛都無意義。我與宋少淵,是什麼情比金堅的有情人嗎?鬧到如今地步,也不知是為何。
好累了。
最終我問宋少淵:「哥,我陪你睡了這麼久,欠你的那些債,還清了嗎?」
宋少淵沉默。沉默好久,說:「還清了。」
「那就不再還了,好嗎?」
「......」
沒聽見他的回答,我從他懷中坐起身,「可以嗎?」
宋少淵看著我,突然冷冷地笑了一下:
「我還以為最後說『夠了』的人會是我,我一直在想,我該在什麼時候覺得,你真正地還夠了。」
我不明白他說這話的意思,不過很快,他就明確地給了我答案:
「可以。
「你自由了。」
宋少淵離開了。
我看著手術室上亮起的紅燈,過了很久,才意識到自己視野里的紅色早已變得一片模糊。
我低下了頭。
將臉深深地埋進雙手之中。
不久,手術結束,我媽被轉至病房。醫生說傷勢無大礙,但需好好修養。
第二日,我託人將大哥大還給宋少淵。這電話我從來也只拿來跟他聯繫,以後聯繫必定少了,也或者根本就無需再聯繫,這麼貴的東西,留在身邊好像沒什麼用。
之後我的生活一下子變得特別平靜。
就連李世瑋都很長一段時間沒再搞什麼事。
宋少淵那邊大概是找過他,照片什麼的,他也沒再提過。
奇怪,原來真會有許多事情發生了,卻如同從未發生。
我的這個家,仍像從前一樣。我、我媽、舅舅,即使每兩個人之間,都那樣激烈地鬧過一場,可到頭來,兜兜轉轉,我們還是心平氣和地坐在一起吃飯。喜歡不喜歡,介懷不介懷的,都不重要,只要沒有殘殺彼此,日子總是這麼過下去。
而宋少淵,確實再也沒有聯繫過。
港城太小,倒也有些不期然的偶遇。
只是又能怎樣呢?
笑眯眯地打招呼,喊一聲「哥」罷了。
19
轉眼一年的時間就過去,日曆一撕撕到年底。
近來李世瑋春風得意,又神神秘秘,說是跟人合夥做了筆不錯的生意,掙了點小錢,在我面前恨不得都用鼻孔說話。我講他別是在搞什麼違法犯罪的東西,當心哪天二進宮,樂極生了悲,我媽就狠狠拍我的頭。
「你舅舅肯做生意是好事,你別說風涼話。」
我撇嘴。江山易改,本性難移,總之我不看好他。
這日李世瑋又煩我,一張報紙伸到我眼前,狂抖,我以為他又要同我吹什麼經濟形勢,莫名其妙,看也不看,便用手撥開。
「看看,你以前的姘頭,這就有新歡了,嘖嘖,轟轟烈烈,還登上報紙哦。」
我抬了抬眼皮,見「黑社會少東」、「賭王小兒子」、「同性戀情」之類的字眼,不甚感興趣地把報紙揉成一團,丟了。
不就是宋少淵和澳城那個簡潼之間那點破事,花邊小報來來回回都寫一個月了,也沒見寫出什麼花來。拍的那些照片,無非就是兩人走得近些,最最曖昧的也就是簡潼說話時,宋少淵附耳過去聽,怎麼,如今狗仔都是這個水平嗎?
我譏諷地說:「這些遠不及舅舅你當年拍的我和宋少淵的照片勁爆,那些照片底片你留著嗎?你拿去給這些小報記者賣一賣,說不定能談個好價錢,比你現在做的那什麼破生意都掙得多。」
我媽端著果盤走進來,「什麼東西掙得多?」
我和李世瑋便都識趣地止戰,難得地異口同聲:「沒什麼,亂聊。」
不敢在她面前提宋少淵,更不敢在她面前提那些照片。
自從因照片的事大鬧一場,跳樓,又做過手術後,我媽的身體一直不太好,情緒也都時好時壞,不太穩定。
李世瑋講話難聽,但有些話說得不是沒道理。他說他們的媽媽,也就是我外婆,生前就有點精神上的問題,聽說這個病會遺傳,所以現在我們都不想無端端地刺激到我媽。
「哦。對了,阿瑾,」我媽坐下,手指捻起果盤裡的一顆車厘子,「你說有朋友在遊輪上開跨年 Party,約你一起,你還有哪個朋友那麼有錢?真是朋友嗎?」
「……」我有些無奈,「媽,這麼多年你教我積極社交,還不知我認識的有錢人多嗎?人家就是愛熱鬧,這才廣發邀請,我也是想維護好關係,不想駁了人家面子,你又想什麼?」
我媽幽幽說:「我想什麼,還不是怕你又被誰金屋藏嬌了。」
「……金屋藏嬌不是這麼用。」
「哈哈哈哈哈!」李世瑋嘲笑得很大聲,「我說阿瑾你是得小心些,你這麼靚仔,說不定真的就有人又想藏你啊,那些少爺小姐玩得都很花的,你——」
「你閉嘴!顧著你自己吧。」
......
我確實是把這個 Party 當作拓展人脈的渠道去的,我也不知有那麼巧,竟在 Party 上遇見了宋少淵和簡潼。
簡潼我不認識,但他是個名人,幾乎沒人不知道他是澳城賭王家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小兒子。
他應該只比宋少淵小個一兩歲,個子也很高,但長了張娃娃臉,眼睛大大圓圓的,笑起來唇邊一對酒窩,顯年紀小。
多認識個人總沒壞處。我拿了杯香檳,拉了個關係比較好的朋友,走上前去。
先從認識的人招呼起,我笑著喊了宋少淵一聲:「哥。」
然後才朝簡潼伸手,「簡少爺,你好,初次見面,我是宋文瑾。」
簡潼看起來很吃驚,和我握了手後,輕輕撞了撞宋少淵的肩膀,很親昵的動作,「都姓宋,少淵,這是你弟弟?」
宋少淵看了看我,看了看我身邊的人,才說:「嗯,是我弟弟。」
簡潼是個比較活躍的性格,又仔細看了看我,笑,「你們看起來不太像哦,不過該說是你們家基因好嗎?都是難得的帥哥。」
宋少淵沒有解釋,我們向來是不對解釋這個的。
於是我也只是沖簡潼笑了一下,「謝謝。」
之後簡潼問我年齡,我說我比我哥小六歲,簡潼就挑眉說:「那你比我小,你也該叫我一聲哥。」
我從善如流:「哥。」
宋少淵冷道:「讓你叫聲哥還真容易。」
我沖他眨眨眼睛,用開玩笑的口吻調劑著:「放心哥,就算在外面有很多哥哥,你也是我唯一的親哥。」
「……誰是你親哥。」
宋少淵轉身走了。
20
一整晚,簡潼和宋少淵可以說是形影不離。看得出來他對宋少淵確實有意,看在我是宋少淵弟弟的份上,便也熱情地同我閒聊。
只可惜我提供不了什麼有價值的信息給他。我同宋少淵之間,只有一籮筐的破事,一籮筐的恩怨。
夜了,我喝多了酒有些犯困,便離開了一樓甲板,往樓上的房間走。
三樓遇見阿龍,神色焦慮,在樓梯邊團團轉。
阿龍是宋少淵手底下的人,也是今夜 Party 的保鏢之一,我們認識。見到他這副模樣,我奇怪地問他:「出什麼事了嗎?」
阿龍幾次三番欲言又止,最後還是說:「我看見有人往淵哥的酒里落了藥,然後那群人起著哄讓簡少爺把他送回房間了,我......我不知道要不要去敲門看看情況。」
「萬一,我說萬一啊,他們兩個借這個機會就……那什麼,我是不是算多管閒事啊?」
「可我明明看見有人落了藥,又不管不問,淵哥知道以後會罵死我的。」
「......」
靠,我實在忍不住爆粗口,真他媽的有病!
哪有撮合別人靠下藥的?
這幫少爺玩得也太離譜了,根本是唯恐天下不亂吧!
我捏了捏拳頭,問了阿龍房號,衝到房間門口。
剛抬手想敲門,又頓住。
萬一萬一,萬一宋少淵其實很願意呢?
簡潼長得好,家世好,又對他痴心,和他簡直不要太合適。
簡潼肯定也很願意做他的解藥。
宋少淵喜歡男人,又是個正常男人,中了藥,身旁又有願意的人,好像沒什麼拒絕的道理。
我猶豫著,房裡忽然傳來很大的動靜。我心裡一瞬間酸得厲害,想走都邁不出步。
受不了!
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!
不知道也就罷了,知道了,站在門口了,我怎麼能忍住不敲這個門?
反正下藥也不是什麼光明磊落的事,今日我就偏管這個閒事!
不想了,我立刻屈起指節敲了幾下門。
「哥!」
「哥!」
「哥你還好嗎?」
沒得到回應,索性變成用力拍。
「宋少淵!宋少淵!」
「宋少淵你——」
門「轟」地一聲開了。
宋少淵站在門裡,上半身赤裸,渾身濕透,一雙眼睛血絲遍布,紅得不正常。
「你幹什麼?」他用很沙啞的聲音問我。
我聽見房間裡有奇怪的聲音,直接越過他往裡面走,震驚地發現簡潼衣衫不整——但被宋少淵用繩子綁起來了。
「阿瑾!」他掙扎著,「快幫我把繩子解開!」
我有些傻眼,走上前去給他解開繩結,他起身整理好自己的衣服,一揚手就給了宋少淵一拳。
簡潼臉通紅,眼睛裡含了點淚,說:「宋少淵,我從來沒有被人這麼羞辱過!」
「對不住,我也只是希望你冷靜點。」
「你這樣看不上我,我也沒必要再自作多情!」
簡潼怒氣沖沖地離開。
門關上後,我突然就尷尬起來,乾笑一聲,「你們兩個……到底誰中藥啊?」
「知道我中藥還主動送上門來?」
宋少淵用力將我摜在牆上。他的身體很燙,就連浸了水的褲子都散出一股熱氣。敲門時我沒考慮後果,此刻對上他那雙被慾望燒得通紅的眼睛,有些慌了。
我硬著頭皮問:「你、你還好嗎?」
宋少淵咬了咬牙,汗水從他的額頭中間滾下來,「你覺得呢?」
說完他把我狠狠往旁邊一推,「快滾!」
他逕自走進浴室,打開了花灑。我跟著走到門口,水珠噼里啪啦地飛濺,濺上我的臉,很涼。
無事發生,其實我是該走了。
但我看著他,就有什麼東西將我釘在原地。
「不走?」宋少淵在水簾中看我一眼,然後不再理會,背過身將自己濕漉漉的褲子脫下來,一個微妙的角度,我看見他的右手在做什麼。
他左手扶住了牆壁,指節微微曲著,手背上浮起青筋,一直延伸到他的小臂上去。
水順著他的頭髮、他的背脊、他精窄的腰身向下流,水聲里摻雜著模糊的喘息。
我走進去,關上了浴室門。
「咔嚓」一聲,使得宋少淵回頭。
我張了張嘴,「哥,我幫你。」
......
半浴缸的水,我在與宋少淵激烈的親吻中,推著他跌進去,自己瞬間也被浸透了。
我憋著一股力氣,抓住宋少淵飽滿的胸肌跨坐在他身上。宋少淵亦十分用力地掐著我的腰。
痛苦到極致是種快感,快感到極致便也是痛苦。深深地感覺到他時,我似乎是痛苦了。
人們總是很快地墜入愛河,很快地分開,相愛難道不是好簡單的一件事;或如簡潼一般,「你看不上我,我便不自作多情」,放手難道不是好簡單的一件事,為何我和宋少淵之間,就那樣複雜?
然而又慶幸於那點複雜。
曾經不甘於只喊一聲「哥」,如今卻想,至少至少,還可以叫一聲哥。
「哥。」
我呢喃著,吻住他。
這其實是我們最珍貴的聯結。
21
波濤浪涌整整一夜都未平息。
結束後我原本想撐著不閉眼,趁宋少淵睡去就先行離開,再做無事發生。誰知他竟是假寐。我剛一掀被,腰就被他手臂勒住,聽見他說:「睡覺。」
我被他強行按住躺了回去。
「不累嗎?有事睡醒再說,現在睡覺。」
本來也很倦了,我到底沒撐住,在他懷裡睡了過去。
醒來時已是下午,宋少淵不在房間。我穿好衣服下到一樓,看見宋少淵坐在沙發上,表情很冷。而他身前站著的那幾個年輕些的,都是平日裡行事張揚被人捧上天的大少爺,此刻,他們個個垂著頭,面上儘是宿醉後褪不去的疲倦,還有說不出的心虛和尷尬。
「淵哥,真的對不住,我們這不是以為你和潼哥……就差臨門一腳嗎。」
「我們有分寸的,就只往你杯里放了少少一點,真的,就只是助助興的程度!」
只是少少一點?
我懷疑。宋少淵明明一個晚上都很......
「怎麼?」宋少淵冷冷地抬起眼皮,「少少一點就不是給我下藥了?非要我慾火焚身暴斃而亡,你們才覺得自己闖了大禍?」
那幾人竟都有些怕他的樣子,聽他這麼說就著了慌,最後一絲殘存的困意都沒了,爭先恐後地圍上去道歉。
臨近傍晚時,Party 徹底散場,遊輪泊入碼頭。
下船後宋少淵把車開到我身邊。他沒帶司機,自己開的車。我見周圍不少人,扭扭捏捏也奇怪,就拉開副駕駛的車門上去了。
路上也沒說什麼。
我好奇問了他一句,那幾個下藥的你這麼說兩句就算完了?他聽完只一聲冷笑,我就懂了。
肯定是沒完。礙於各家面子他沒撕破臉,但後頭他總能找到辦法整他們。
「有哪裡不舒服嗎?」宋少淵突然問。
我沒想到他還提這個,抿了抿唇,說:「沒有。」
大轉彎,宋少淵專注地看著前路,手上轉著方向盤,聲音淡淡飄過來,「昨夜敲門那麼急,怕我跟簡潼亂性?」
我轉頭朝他看去,他恰巧也側過臉,視線相撞,他追逼:「嗯?」
我便說:「是阿龍說看見有人朝你杯里落藥,我又不知什麼藥……我還是會擔心你的,哥。」
宋少淵輕笑一聲,過了一會兒,才又說:「那算我欠你一次,畢竟你還是幫我很大的忙。」
天邊夕陽行將燒盡,汽車駛入繁華些的路段,馬路邊已有少數霓虹招牌亮起,各色燈光擠占視線。
港城總是這樣地繚亂。
我望著窗外飛逝而過的街景,忽而視線一定。
是......我媽?
她幾乎不來這樣的舊城區,怎還站在人潮湧動的街頭,與一個陌生的男人——
不,不對,不是陌生男人。
是李世瑋。
他做了些偽裝,但我們做了二十幾年的親人,他的身形我太熟悉。
我不禁想起前些天,我媽對我抱怨說,阿瑋好一陣子都無音信,也不來看她,不知是做什麼去了。
當時我未在意,畢竟我這個舅舅從前就如此,沉迷賭場或花天酒地,誰知他是不是又玩得忘記今夕何夕?
如今他又是在搞什麼神秘?
我忍不住叫宋少淵停了車,坐在車裡遠遠地觀察。
沒多久,兩人說完了話,我媽似乎不舍,抓住他的手好一會兒,李世瑋拍拍她,似是安撫,然後轉過身,壓低帽檐,匯入人流。
 喬峰傳 • 3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K次觀看 游啊游 • 9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9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11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11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8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8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9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90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6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90次觀看
喬峰傳 • 9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3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7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7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6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6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38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38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6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6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38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38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3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3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23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23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8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80次觀看 卞德江 • 90次觀看
卞德江 • 9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6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6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12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12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6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6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13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130次觀看 游啊游 • 80次觀看
游啊游 • 8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6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60次觀看 滿素荷 • 80次觀看
滿素荷 • 80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