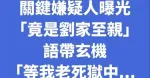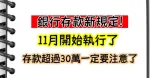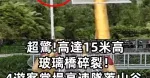4/4
下一頁
漢文帝劉恆:天生的帝王,其腹黑和權謀手段,連劉邦也得直呼內行

4/4
這位寵妃的待遇一度逾越禮制,直到袁盎以"人彘之禍"的典故進諫,劉恆才不情願地收斂了些許。
這種矛盾同樣體現在經濟政策上,他允許民間私鑄錢幣,還賜給寵臣鄧通銅山鑄錢之權,卻又在全國推行"三十稅一"的輕徭薄賦。
在軍事方面,劉恆的選擇更顯複雜。
當匈奴鐵騎突破蕭關、烽火照甘泉時,這位平日溫和的皇帝竟執意要御駕親征。
群臣的勸阻全然無效,最後還是薄太后出面才將他攔下。
這場未遂的親征暴露出劉恆性格中鮮為人知的一面,在謹慎算計的外表下,依然流淌著劉邦那種賭徒般的冒險血液。
這或許也是帝王的必要血性。
到了晚年,劉恆對鬼神的痴迷日益加深。
曾經精於權術的帝王,如今卻對術士的預言言聽計從,當這個騙子最終被揭穿時,劉恆不僅處死了新垣平,還恢復了廢除多年的"夷三族"酷刑。
這個殘酷的決定與他早年輕刑薄賦的形象形成鮮明對比,暴露出仁政表象下始終存在的鐵血本質。
死亡來臨之際,劉恆展現出了最後的清醒。
他的遺詔顛覆了傳統帝王喪儀的鋪張,要求喪期從簡,允許百姓婚嫁飲酒,陵墓只用瓦器。
這份遺詔與其說是節儉,不如說是一個精於算計的統治者最後的政治表演。
與其讓百姓為他的死亡勞民傷財,不如用這份"恩典"換取民心的長久擁戴。
果然,數百年後的綠林赤眉起義軍經過霸陵時,都主動繞道而行,以示對這位"仁君"的敬意。
劉恆留給歷史的,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仁君形象,而藏在霸陵深處的,才是一個真實而複雜的帝王靈魂。
人們總是調侃,若是劉邦看到他的所作所為,恐怕也得直呼內行。
但不可否認,這是一個想當出色的皇帝,一個典型的政治權謀家。
這種矛盾同樣體現在經濟政策上,他允許民間私鑄錢幣,還賜給寵臣鄧通銅山鑄錢之權,卻又在全國推行"三十稅一"的輕徭薄賦。
在軍事方面,劉恆的選擇更顯複雜。
當匈奴鐵騎突破蕭關、烽火照甘泉時,這位平日溫和的皇帝竟執意要御駕親征。
群臣的勸阻全然無效,最後還是薄太后出面才將他攔下。
這場未遂的親征暴露出劉恆性格中鮮為人知的一面,在謹慎算計的外表下,依然流淌著劉邦那種賭徒般的冒險血液。
這或許也是帝王的必要血性。
到了晚年,劉恆對鬼神的痴迷日益加深。
曾經精於權術的帝王,如今卻對術士的預言言聽計從,當這個騙子最終被揭穿時,劉恆不僅處死了新垣平,還恢復了廢除多年的"夷三族"酷刑。
這個殘酷的決定與他早年輕刑薄賦的形象形成鮮明對比,暴露出仁政表象下始終存在的鐵血本質。
死亡來臨之際,劉恆展現出了最後的清醒。
他的遺詔顛覆了傳統帝王喪儀的鋪張,要求喪期從簡,允許百姓婚嫁飲酒,陵墓只用瓦器。
這份遺詔與其說是節儉,不如說是一個精於算計的統治者最後的政治表演。
與其讓百姓為他的死亡勞民傷財,不如用這份"恩典"換取民心的長久擁戴。
果然,數百年後的綠林赤眉起義軍經過霸陵時,都主動繞道而行,以示對這位"仁君"的敬意。
劉恆留給歷史的,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仁君形象,而藏在霸陵深處的,才是一個真實而複雜的帝王靈魂。
人們總是調侃,若是劉邦看到他的所作所為,恐怕也得直呼內行。
但不可否認,這是一個想當出色的皇帝,一個典型的政治權謀家。
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