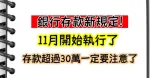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紀曉嵐嫁女,陪嫁一個破碗,被恥笑十年女婿想摔碗,看到碗底傻眼

2/3
來年春天,他滿懷著一雪前恥的決心,走進了貢院。可放榜那天,他在人群中找了整整三個時辰,把那張巨大的杏黃榜單從頭看到尾,又從尾看到頭,始終沒有找到「祝汝昌」三個字。
名落孫山。
這個打擊對祝汝昌來說是毀滅性的。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,一頭栽倒在床上,把自己關在書房裡,整整三天三夜沒吃沒喝。他開始瘋狂地懷疑自己,是不是自己真的就是個繡花枕頭,中看不中用?是不是岳父早就看出來他不是科舉的料,所以才用那隻破碗來暗示他,他祝汝昌的命,就跟那隻碗一樣,註定是殘缺的,是上不了台面的。
紀筠心疼得不得了,卻不敢多勸。她只是默默地把飯菜熱了一遍又一遍,放在書房門口。直到第三天夜裡,祝汝昌才打開門,鬍子拉碴,雙眼通紅,像一瞬間老了十歲。
紀筠連忙扶住他,眼淚簌簌地往下掉:「夫君,你可算出來了。」
祝汝昌看著她,嘴唇哆嗦了半天,才說出一句話:「我是不是……真的很沒用?」
紀筠用力搖頭,哽咽著說:「不!一次失利算不得什麼。你的才學,我信,爹也信。我們還年輕,大不了從頭再來!」
妻子的溫柔和信任,是祝汝昌在那段黑暗日子裡唯一的光。他重新振作起來,一邊讀書,一邊為了餬口,放下讀書人的架子,去給大戶人家的子弟做啟蒙先生,賺取微薄的束脩。有時實在揭不開鍋了,他甚至會到街頭巷尾,支個小攤,替不識字的人寫信、寫對聯。
每當他鋪開紙筆,迎著路人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時,他就覺得自己的臉頰像被火燒一樣滾燙。他曾經是何等的心高氣傲,如今卻落魄至此。
時光荏苒,又是幾年過去。祝汝昌接連又參加了兩次科考,每一次都拼盡了全力,可每一次都名落孫山。他的文章並非不好,只是似乎總差了那麼一點運氣,又或者,他的文風總是與主考官的喜好背道而馳。
家裡的積蓄徹底花光了,紀筠的首飾也當得一乾二淨。日子過得愈發捉襟見肘,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。
那年冬天,京城下了好大一場雪,滴水成冰。他們三歲的兒子,也不知是夜裡著了涼,還是餓得久了傷了元氣,突然發起高燒,渾身滾燙,小臉燒得通紅,說起了胡話。
紀筠抱著孩子,急得心如刀絞,眼淚一串串地往下掉。可摸遍了家裡所有的角落,也湊不出半吊錢來請個大夫。
「夫君,怎麼辦啊?孩子……孩子他……」紀筠的聲音裡帶著絕望的哭腔。
祝汝昌看著在妻子懷裡昏睡不醒的兒子,只覺得五臟六腑都像被一隻大手攥住了,痛得無法呼吸。他咬了咬牙,脫下身上唯一還算體面的棉布長衫,用那件單薄的夾襖裹住身子,啞著嗓子說:「你等著,我……我去想辦法!」
他衝進漫天大雪裡,深夜的寒風像刀子一樣刮在他臉上。他跑遍了半個京城,最後來到一家還亮著燈的當鋪。當鋪的朝奉睡眼惺忪地接過他那件洗得發白的舊長衫,在燈下翻來覆去地看了半天,輕蔑地撇了撇嘴,伸出五個指頭:「死當,五十文。愛當不當。」
五十文錢!連一副最便宜的退燒藥都買不到!
祝汝昌的心徹底沉入了谷底。他拿著那件長衫,如同行屍走肉一般,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家走。雪花落在他的頭髮上、肩膀上,很快積了白白的一層,他卻感覺不到絲毫寒冷,因為他的心,已經比這冰雪還要冷。
他推開家門,看到屋裡的一幕,讓他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紀筠正用厚厚的破棉被把孩子裹得嚴嚴實實,自己也穿戴整齊,看樣子,是準備抱著孩子回娘家求助。
一股難以言喻的屈辱和憤怒,瞬間衝垮了祝汝昌的理智。
他「砰」的一聲關上門,嘶吼道:「不許去!」
紀筠被他嚇了一跳,回過頭,淚眼婆娑:「汝昌,孩子快不行了!我們不能再撐著了,我……」
「我說了不許去!」祝汝昌幾步衝上前,一把攔住她,雙眼赤紅,「我祝汝昌就是死,就是看著孩子病死,也絕不回去受他們的白眼!絕不!」
他的目光掃過屋角,落在了那個專門用來放置破碗的小木架上。這些年,不管搬到哪裡,紀筠都執意帶著這隻碗,說那是爹給的念想。可在祝汝昌眼裡,這碗就是他恥辱的根源,是他十年痛苦的象徵。
他的眼神陡然變得瘋狂起來。
他一步步走過去,一把將那隻破碗抓在手裡,碗口那處豁口硌得他手心生疼。他轉過身,對著紀筠,聲音顫抖而猙獰:「山窮水盡?你告訴我,我們現在還不夠山窮水盡嗎?!啊?!你爹不是說,到了那個時候,就能懂了嗎?我今天倒要看看,這碗里到底藏著什麼救我們全家性命的天大的道理!」
紀筠嚇得臉色慘白,扔下孩子就撲過來,死死抱住他的胳膊,哭著哀求:「夫君,不要!不要啊!爹說的是餓到要討飯的時候!我們……我們還沒到那一步啊!」
「有什麼區別!」祝汝昌狂亂地掙扎著,「在他們眼裡,我們早就跟討飯的沒區別了!」
孩子的哭聲,妻子的哀求聲,和他自己胸中的怒吼交織在一起。他高高地舉著碗,渾身顫抖,青筋暴起。最終,看著妻子那張絕望而悲傷的臉,他手臂的力量還是一點點地鬆懈了下去。
他「哐當」一聲,將碗扔回了木架上,然後頹然地滑坐在地,雙手插入頭髮,發出了困獸一般的低嚎。
他眼中的那份曾支撐著他的希望之火,在這一刻,似乎徹底熄滅了。他覺得,這隻碗,這個人,這一切,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,一個專門用來折磨他的、冰冷而殘酷的枷鎖。
03
光陰似水,一去不返。
彈指一揮間,十年過去了。
京城的繁華一如往昔,甚至更勝往昔。只是這份繁華,與祝汝昌再無半點關係。
十年的歲月,像一把最無情的刻刀,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。他已經從一個眉目疏朗、風華正茂的青年,變成了一個兩鬢染霜、眼神麻木的中年人。他臉上的線條變得僵硬,背脊也不再挺拔,常年累月的窘迫和抑鬱,讓他的眉宇間刻下了一道化不開的「川」字。
他徹底放棄了科舉。那條通往青雲之路的獨木橋,他走了三次,摔了三次,摔得他筋斷骨折,再也爬不起來了。如今,他每日靠給街坊鄰里抄抄書,教幾個調皮搗蛋的蒙童念念「人之初」,來換取一些微薄的收入,勉強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。
紀筠也不再是當年那個溫婉如水的新嫁娘。繁重的家務和常年的營養不良,讓她的雙手變得粗糙,眼角也爬上了細密的皺紋,容顏早已不復當年的光彩。可唯一不變的,是她那雙看著丈夫和兒女時,依舊溫柔如水的眼眸。
他們有了一兒一女,本該是兒女繞膝的溫馨景象,卻因為貧窮,讓這個家始終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。
生活的重壓,不只磨去了他們的青春,更在他們這對曾經恩愛不疑的夫妻之間,鑿出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。他們之間的對話越來越少,沉默越來越多。
祝汝昌的心,在長達十年的折磨中,已經變得扭曲。他變得異常敏感、自卑,同時也暴躁易怒。他最恨別人在他面前提起他的岳父是紀曉嵐,也最恨別人用同情的眼光看他。在他看來,那同情就是最尖銳的嘲諷。
有時候,他會花掉家裡僅有的幾文錢,去打一壺劣質的燒酒,喝得酩酊大醉。醉了之後,他會指著屋角那隻破碗,顛三倒四地咒罵,罵紀曉嵐這個老狐狸故弄玄虛,毀了他的一生;罵自己當年瞎了狗眼,才會興高采烈地跳進這個精心設計的羞辱陷阱里。
他甚至開始覺得,紀筠那十年如一日的溫柔和堅韌,都像是在無聲地諷刺他的無能和失敗。他會無端地猜忌,覺得她是不是早就後悔了,是不是在心裡瞧不起他,只是礙於大家閨秀的教養,才沒有說出口。
這種猜忌像毒蛇一樣,啃噬著他僅存的理智。
紀筠默默地承受著丈夫所有的壞脾氣。她知道他心裡苦,比任何人都苦。她試圖去安慰,去開解,可她所有的言語,在殘酷的現實面前,都顯得那麼蒼白無力。
她最怕的,不是挨餓受凍,而是眼睜睜地看著丈夫那曾經比天還高的心氣,一天天消亡,最後化為一灘死灰。
她也曾幾次三番地想,要不就拉下臉,回娘家去求助。可每次她一開口,都會遭到祝汝昌暴風驟雨般的拒絕。
「要去你去!我祝汝昌就算是餓死街頭,也絕不吃他們紀家的一口嗟來之食!」
有一次,恰逢紀老太太壽辰,紀府派了管家,送來幾匹上好的布料和一包沉甸甸的銀子。祝汝昌當時正在院子裡劈柴,看到管家那張熟悉的、帶著幾分客氣又帶著幾分疏離的臉,他心頭的無名火「騰」地就燒了起來。
他沒等管家把話說完,就衝上去,奪過那包東西,當著所有街坊鄰居的面,狠狠地扔到了大門外,大吼道:「拿回去!告訴你們家大人,我們還沒餓死,用不著他紀大學士的施捨!」
銀子和布料散落一地,管家尷尬地站在那裡,臉上一陣紅一陣白。街坊們指指點點,議論紛紛。
這件事,徹底傷透了紀筠的心。她第一次和祝汝昌爆發了激烈的爭吵。可祝汝昌就像一頭被激怒的困獸,根本聽不進任何話。
夫妻間的信任裂痕,就這樣越來越大。
真正讓這道裂痕擴大到無法彌合地步的,是兩件接踵而至的事。
第一件,是他們的兒子祝念祖。念祖在學堂里,因為外公是大學士,父親卻是個窮困潦倒的教書匠,常常被那些富家子弟嘲笑。
「瞧,他就是那個『破碗女婿』的兒子!」「他外公家有金山銀山,他爹連支新毛筆都買不起,真好笑!」
孩子小,不懂大人世界的複雜,只覺得委屈。他哭著跑回家,拉著祝汝昌的衣角問:「爹,他們為什麼都笑話我?為什麼外公是大官,我們家卻這麼窮?」
這句童稚的問話,像一把錐子,狠狠地扎在了祝汝昌的心上。他無言以對,臉上青一陣白一陣,十年積壓的羞辱和憤懣在這一刻徹底爆發。他揚起手,平生第一次,重重地給了兒子一個耳光。
名落孫山。
這個打擊對祝汝昌來說是毀滅性的。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,一頭栽倒在床上,把自己關在書房裡,整整三天三夜沒吃沒喝。他開始瘋狂地懷疑自己,是不是自己真的就是個繡花枕頭,中看不中用?是不是岳父早就看出來他不是科舉的料,所以才用那隻破碗來暗示他,他祝汝昌的命,就跟那隻碗一樣,註定是殘缺的,是上不了台面的。
紀筠心疼得不得了,卻不敢多勸。她只是默默地把飯菜熱了一遍又一遍,放在書房門口。直到第三天夜裡,祝汝昌才打開門,鬍子拉碴,雙眼通紅,像一瞬間老了十歲。
紀筠連忙扶住他,眼淚簌簌地往下掉:「夫君,你可算出來了。」
祝汝昌看著她,嘴唇哆嗦了半天,才說出一句話:「我是不是……真的很沒用?」
紀筠用力搖頭,哽咽著說:「不!一次失利算不得什麼。你的才學,我信,爹也信。我們還年輕,大不了從頭再來!」
妻子的溫柔和信任,是祝汝昌在那段黑暗日子裡唯一的光。他重新振作起來,一邊讀書,一邊為了餬口,放下讀書人的架子,去給大戶人家的子弟做啟蒙先生,賺取微薄的束脩。有時實在揭不開鍋了,他甚至會到街頭巷尾,支個小攤,替不識字的人寫信、寫對聯。
每當他鋪開紙筆,迎著路人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時,他就覺得自己的臉頰像被火燒一樣滾燙。他曾經是何等的心高氣傲,如今卻落魄至此。
時光荏苒,又是幾年過去。祝汝昌接連又參加了兩次科考,每一次都拼盡了全力,可每一次都名落孫山。他的文章並非不好,只是似乎總差了那麼一點運氣,又或者,他的文風總是與主考官的喜好背道而馳。
家裡的積蓄徹底花光了,紀筠的首飾也當得一乾二淨。日子過得愈發捉襟見肘,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。
那年冬天,京城下了好大一場雪,滴水成冰。他們三歲的兒子,也不知是夜裡著了涼,還是餓得久了傷了元氣,突然發起高燒,渾身滾燙,小臉燒得通紅,說起了胡話。
紀筠抱著孩子,急得心如刀絞,眼淚一串串地往下掉。可摸遍了家裡所有的角落,也湊不出半吊錢來請個大夫。
「夫君,怎麼辦啊?孩子……孩子他……」紀筠的聲音裡帶著絕望的哭腔。
祝汝昌看著在妻子懷裡昏睡不醒的兒子,只覺得五臟六腑都像被一隻大手攥住了,痛得無法呼吸。他咬了咬牙,脫下身上唯一還算體面的棉布長衫,用那件單薄的夾襖裹住身子,啞著嗓子說:「你等著,我……我去想辦法!」
他衝進漫天大雪裡,深夜的寒風像刀子一樣刮在他臉上。他跑遍了半個京城,最後來到一家還亮著燈的當鋪。當鋪的朝奉睡眼惺忪地接過他那件洗得發白的舊長衫,在燈下翻來覆去地看了半天,輕蔑地撇了撇嘴,伸出五個指頭:「死當,五十文。愛當不當。」
五十文錢!連一副最便宜的退燒藥都買不到!
祝汝昌的心徹底沉入了谷底。他拿著那件長衫,如同行屍走肉一般,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家走。雪花落在他的頭髮上、肩膀上,很快積了白白的一層,他卻感覺不到絲毫寒冷,因為他的心,已經比這冰雪還要冷。
他推開家門,看到屋裡的一幕,讓他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紀筠正用厚厚的破棉被把孩子裹得嚴嚴實實,自己也穿戴整齊,看樣子,是準備抱著孩子回娘家求助。
一股難以言喻的屈辱和憤怒,瞬間衝垮了祝汝昌的理智。
他「砰」的一聲關上門,嘶吼道:「不許去!」
紀筠被他嚇了一跳,回過頭,淚眼婆娑:「汝昌,孩子快不行了!我們不能再撐著了,我……」
「我說了不許去!」祝汝昌幾步衝上前,一把攔住她,雙眼赤紅,「我祝汝昌就是死,就是看著孩子病死,也絕不回去受他們的白眼!絕不!」
他的目光掃過屋角,落在了那個專門用來放置破碗的小木架上。這些年,不管搬到哪裡,紀筠都執意帶著這隻碗,說那是爹給的念想。可在祝汝昌眼裡,這碗就是他恥辱的根源,是他十年痛苦的象徵。
他的眼神陡然變得瘋狂起來。
他一步步走過去,一把將那隻破碗抓在手裡,碗口那處豁口硌得他手心生疼。他轉過身,對著紀筠,聲音顫抖而猙獰:「山窮水盡?你告訴我,我們現在還不夠山窮水盡嗎?!啊?!你爹不是說,到了那個時候,就能懂了嗎?我今天倒要看看,這碗里到底藏著什麼救我們全家性命的天大的道理!」
紀筠嚇得臉色慘白,扔下孩子就撲過來,死死抱住他的胳膊,哭著哀求:「夫君,不要!不要啊!爹說的是餓到要討飯的時候!我們……我們還沒到那一步啊!」
「有什麼區別!」祝汝昌狂亂地掙扎著,「在他們眼裡,我們早就跟討飯的沒區別了!」
孩子的哭聲,妻子的哀求聲,和他自己胸中的怒吼交織在一起。他高高地舉著碗,渾身顫抖,青筋暴起。最終,看著妻子那張絕望而悲傷的臉,他手臂的力量還是一點點地鬆懈了下去。
他「哐當」一聲,將碗扔回了木架上,然後頹然地滑坐在地,雙手插入頭髮,發出了困獸一般的低嚎。
他眼中的那份曾支撐著他的希望之火,在這一刻,似乎徹底熄滅了。他覺得,這隻碗,這個人,這一切,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,一個專門用來折磨他的、冰冷而殘酷的枷鎖。
03
光陰似水,一去不返。
彈指一揮間,十年過去了。
京城的繁華一如往昔,甚至更勝往昔。只是這份繁華,與祝汝昌再無半點關係。
十年的歲月,像一把最無情的刻刀,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。他已經從一個眉目疏朗、風華正茂的青年,變成了一個兩鬢染霜、眼神麻木的中年人。他臉上的線條變得僵硬,背脊也不再挺拔,常年累月的窘迫和抑鬱,讓他的眉宇間刻下了一道化不開的「川」字。
他徹底放棄了科舉。那條通往青雲之路的獨木橋,他走了三次,摔了三次,摔得他筋斷骨折,再也爬不起來了。如今,他每日靠給街坊鄰里抄抄書,教幾個調皮搗蛋的蒙童念念「人之初」,來換取一些微薄的收入,勉強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。
紀筠也不再是當年那個溫婉如水的新嫁娘。繁重的家務和常年的營養不良,讓她的雙手變得粗糙,眼角也爬上了細密的皺紋,容顏早已不復當年的光彩。可唯一不變的,是她那雙看著丈夫和兒女時,依舊溫柔如水的眼眸。
他們有了一兒一女,本該是兒女繞膝的溫馨景象,卻因為貧窮,讓這個家始終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。
生活的重壓,不只磨去了他們的青春,更在他們這對曾經恩愛不疑的夫妻之間,鑿出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。他們之間的對話越來越少,沉默越來越多。
祝汝昌的心,在長達十年的折磨中,已經變得扭曲。他變得異常敏感、自卑,同時也暴躁易怒。他最恨別人在他面前提起他的岳父是紀曉嵐,也最恨別人用同情的眼光看他。在他看來,那同情就是最尖銳的嘲諷。
有時候,他會花掉家裡僅有的幾文錢,去打一壺劣質的燒酒,喝得酩酊大醉。醉了之後,他會指著屋角那隻破碗,顛三倒四地咒罵,罵紀曉嵐這個老狐狸故弄玄虛,毀了他的一生;罵自己當年瞎了狗眼,才會興高采烈地跳進這個精心設計的羞辱陷阱里。
他甚至開始覺得,紀筠那十年如一日的溫柔和堅韌,都像是在無聲地諷刺他的無能和失敗。他會無端地猜忌,覺得她是不是早就後悔了,是不是在心裡瞧不起他,只是礙於大家閨秀的教養,才沒有說出口。
這種猜忌像毒蛇一樣,啃噬著他僅存的理智。
紀筠默默地承受著丈夫所有的壞脾氣。她知道他心裡苦,比任何人都苦。她試圖去安慰,去開解,可她所有的言語,在殘酷的現實面前,都顯得那麼蒼白無力。
她最怕的,不是挨餓受凍,而是眼睜睜地看著丈夫那曾經比天還高的心氣,一天天消亡,最後化為一灘死灰。
她也曾幾次三番地想,要不就拉下臉,回娘家去求助。可每次她一開口,都會遭到祝汝昌暴風驟雨般的拒絕。
「要去你去!我祝汝昌就算是餓死街頭,也絕不吃他們紀家的一口嗟來之食!」
有一次,恰逢紀老太太壽辰,紀府派了管家,送來幾匹上好的布料和一包沉甸甸的銀子。祝汝昌當時正在院子裡劈柴,看到管家那張熟悉的、帶著幾分客氣又帶著幾分疏離的臉,他心頭的無名火「騰」地就燒了起來。
他沒等管家把話說完,就衝上去,奪過那包東西,當著所有街坊鄰居的面,狠狠地扔到了大門外,大吼道:「拿回去!告訴你們家大人,我們還沒餓死,用不著他紀大學士的施捨!」
銀子和布料散落一地,管家尷尬地站在那裡,臉上一陣紅一陣白。街坊們指指點點,議論紛紛。
這件事,徹底傷透了紀筠的心。她第一次和祝汝昌爆發了激烈的爭吵。可祝汝昌就像一頭被激怒的困獸,根本聽不進任何話。
夫妻間的信任裂痕,就這樣越來越大。
真正讓這道裂痕擴大到無法彌合地步的,是兩件接踵而至的事。
第一件,是他們的兒子祝念祖。念祖在學堂里,因為外公是大學士,父親卻是個窮困潦倒的教書匠,常常被那些富家子弟嘲笑。
「瞧,他就是那個『破碗女婿』的兒子!」「他外公家有金山銀山,他爹連支新毛筆都買不起,真好笑!」
孩子小,不懂大人世界的複雜,只覺得委屈。他哭著跑回家,拉著祝汝昌的衣角問:「爹,他們為什麼都笑話我?為什麼外公是大官,我們家卻這麼窮?」
這句童稚的問話,像一把錐子,狠狠地扎在了祝汝昌的心上。他無言以對,臉上青一陣白一陣,十年積壓的羞辱和憤懣在這一刻徹底爆發。他揚起手,平生第一次,重重地給了兒子一個耳光。
 呂純弘 • 5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