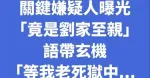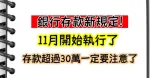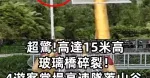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西漢名將一生只打一仗,換中國三百年無人敢犯,一句名言流傳至今

2/3
但即便在最狼狽的時刻,他也沒有賣掉那捆竹簡,那是他唯一的武器,也是他與長安城裡所有汲汲營營之人最大的不同。
某個冬日,陳湯在太官署外替人代寫家書,一手俊逸的字跡和信中引經據典的文采,恰好被路過的富平侯張勃看在眼裡。
這位會識人著稱的貴族停下腳步,與這個衣衫單薄卻談吐不凡的年輕人攀談起來。
從《孫子兵法》到《春秋》微言大義,陳湯對答如流,眼中閃爍著久違的自信光芒。
張勃大為驚嘆,當即將他薦為太官獻食丞,一個掌管宮廷膳食採買的微末小吏。
對別人而言這只是個油水差事,對陳湯卻是通往權力殿堂的第一塊敲門磚。
人人都以為這是鹹魚翻身的好運氣,但命運總會給人當頭一擊。
就在陳湯兢兢業業經營新職位,等待朝廷正式任命時,老家傳來噩耗,父親病故了。
按照漢律,官員必須棄官守孝三年,否則就是大不孝之罪。
回去,意味著三年後長安早已物是人非,誰還會記得一個寒門小吏?
不回去,就是賭上全部前程甚至性命……
最終,他顫抖著燒掉了那捲報喪竹簡,哪怕這個決定日後讓他付出慘痛代價。
悲劇的是,秘密終究沒能守住。
不久後,仇家告發,漢元帝震怒於他「毀傷教化」,不僅將他投入詔獄,連舉薦人張勃也被削爵罰俸。
自薦出使
詔獄的鐵門在身後哐當一聲關閉,長安街市依舊喧囂,但陳湯的世界已經天翻地覆。
失去官職、背負污名,這個曾經懷揣青雲之志的年輕人此刻只剩下一個念頭,絕不能就此沉淪。
他在獄中反覆推演當今天下大勢,最終將目光投向了西域。
那裡有烽煙,有戰鼓,更有無數野心和機會在翻滾。
此時的漢帝國,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尷尬局面。
宣帝時期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,呼韓邪單于歸附稱臣,而郅支單于則率部西遷至康居一帶。
他狡詐殘暴,憑藉騎兵優勢不斷蠶食西域小國,甚至公然羞辱漢使。
消息傳回長安,舉朝譁然,可龍椅上的漢元帝卻顯得猶豫不決。
這位深受儒家教化影響的皇帝更傾向於遣使交涉,甚至多次派人索要遇難使臣遺骨,仿佛這樣就能維護天朝尊嚴。
郅支單于看透了漢朝的軟弱,氣焰越發囂張。
西域諸國見漢朝遲遲不敢動手,逐漸開始搖擺。
烏孫、大宛等國使者頻頻出入康居王庭,車師等國更是暗中輸送糧草給匈奴騎兵。
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,陳湯通過舊友牽線,重新獲得了郎官的職位。
雖然只是秩比三百石的小官,卻讓他獲得了站立在朝堂末位的資格。
當大鴻臚又一次奏報郅支單于斬殺漢使、襲擾屬國時,滿朝文武鴉雀無聲。
老成持重的大臣們眼觀鼻鼻觀心,誰都知道這是個燙手山芋,打贏了未必有功,打輸了必定獲罪。
就在這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中,一個清朗的聲音突然從殿尾響起:「臣湯,願往。」
陳湯穩步出列,俯身行禮:
「郅支單于虐殺使者,藐視漢威,若不加征討,西域必叛,臣請出使,宣大漢天威於絕域。」
這番話擲地有聲,與其說是請命,不如說是對整個朝廷怯懦的無聲指責。
漢元帝似乎被這份勇氣打動,更可能是急於找人收拾爛攤子,當即准奏,任命陳湯為西域副校尉,與西域都護甘延壽一同出使。
踏出玉門關的那一刻,陳湯才真正體會到什麼是「絕域」。
茫茫戈壁連接著天際,熱風卷著沙粒抽打在臉上。
但比自然環境更惡劣的是人心。
他們先後抵達烏孫、大宛等國,那些國王雖然禮儀周到,眼神卻閃爍不定。
這些國家既害怕匈奴鐵騎,更懷疑漢朝的實力。
終於在一個夜晚,陳湯掀開了甘延壽的帳幕。
地圖在油燈下鋪開,他的手指重重點在康居的位置:
「郅支單于殘暴失道,烏孫、大宛皆懷二心,今其遠遁萬里,士卒疲敝,正是用兵之時。」
他提出一個大膽的計劃,就地徵調西域屬國兵馬,聯合漢朝屯田吏士,趁匈奴立足未穩發動奇襲。
甘延壽聞言大驚:「不發虎符而擅調大軍,這是滅族之罪!」
陳湯卻凝視著跳動的燈火,一字一句道:
「郅支單于視漢如無物,西域各國離心離德,若等朝廷往復辯論,恐西域已非漢有。」
兩個漢朝使臣相對無言,遠方的地平線上,康居國的燈火如鬼火般明滅不定,那裡有囂張的匈奴單于,有被辱殺的漢使亡魂,更有一個帝國搖搖欲墜的尊嚴。
矯詔出兵
甘延壽病倒的消息傳來時,陳湯正在擦拭佩劍。
某個冬日,陳湯在太官署外替人代寫家書,一手俊逸的字跡和信中引經據典的文采,恰好被路過的富平侯張勃看在眼裡。
這位會識人著稱的貴族停下腳步,與這個衣衫單薄卻談吐不凡的年輕人攀談起來。
從《孫子兵法》到《春秋》微言大義,陳湯對答如流,眼中閃爍著久違的自信光芒。
張勃大為驚嘆,當即將他薦為太官獻食丞,一個掌管宮廷膳食採買的微末小吏。
對別人而言這只是個油水差事,對陳湯卻是通往權力殿堂的第一塊敲門磚。
人人都以為這是鹹魚翻身的好運氣,但命運總會給人當頭一擊。
就在陳湯兢兢業業經營新職位,等待朝廷正式任命時,老家傳來噩耗,父親病故了。
按照漢律,官員必須棄官守孝三年,否則就是大不孝之罪。
回去,意味著三年後長安早已物是人非,誰還會記得一個寒門小吏?
不回去,就是賭上全部前程甚至性命……
最終,他顫抖著燒掉了那捲報喪竹簡,哪怕這個決定日後讓他付出慘痛代價。
悲劇的是,秘密終究沒能守住。
不久後,仇家告發,漢元帝震怒於他「毀傷教化」,不僅將他投入詔獄,連舉薦人張勃也被削爵罰俸。
自薦出使
詔獄的鐵門在身後哐當一聲關閉,長安街市依舊喧囂,但陳湯的世界已經天翻地覆。
失去官職、背負污名,這個曾經懷揣青雲之志的年輕人此刻只剩下一個念頭,絕不能就此沉淪。
他在獄中反覆推演當今天下大勢,最終將目光投向了西域。
那裡有烽煙,有戰鼓,更有無數野心和機會在翻滾。
此時的漢帝國,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尷尬局面。
宣帝時期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,呼韓邪單于歸附稱臣,而郅支單于則率部西遷至康居一帶。
他狡詐殘暴,憑藉騎兵優勢不斷蠶食西域小國,甚至公然羞辱漢使。
消息傳回長安,舉朝譁然,可龍椅上的漢元帝卻顯得猶豫不決。
這位深受儒家教化影響的皇帝更傾向於遣使交涉,甚至多次派人索要遇難使臣遺骨,仿佛這樣就能維護天朝尊嚴。
郅支單于看透了漢朝的軟弱,氣焰越發囂張。
西域諸國見漢朝遲遲不敢動手,逐漸開始搖擺。
烏孫、大宛等國使者頻頻出入康居王庭,車師等國更是暗中輸送糧草給匈奴騎兵。
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,陳湯通過舊友牽線,重新獲得了郎官的職位。
雖然只是秩比三百石的小官,卻讓他獲得了站立在朝堂末位的資格。
當大鴻臚又一次奏報郅支單于斬殺漢使、襲擾屬國時,滿朝文武鴉雀無聲。
老成持重的大臣們眼觀鼻鼻觀心,誰都知道這是個燙手山芋,打贏了未必有功,打輸了必定獲罪。
就在這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中,一個清朗的聲音突然從殿尾響起:「臣湯,願往。」
陳湯穩步出列,俯身行禮:
「郅支單于虐殺使者,藐視漢威,若不加征討,西域必叛,臣請出使,宣大漢天威於絕域。」
這番話擲地有聲,與其說是請命,不如說是對整個朝廷怯懦的無聲指責。
漢元帝似乎被這份勇氣打動,更可能是急於找人收拾爛攤子,當即准奏,任命陳湯為西域副校尉,與西域都護甘延壽一同出使。
踏出玉門關的那一刻,陳湯才真正體會到什麼是「絕域」。
茫茫戈壁連接著天際,熱風卷著沙粒抽打在臉上。
但比自然環境更惡劣的是人心。
他們先後抵達烏孫、大宛等國,那些國王雖然禮儀周到,眼神卻閃爍不定。
這些國家既害怕匈奴鐵騎,更懷疑漢朝的實力。
終於在一個夜晚,陳湯掀開了甘延壽的帳幕。
地圖在油燈下鋪開,他的手指重重點在康居的位置:
「郅支單于殘暴失道,烏孫、大宛皆懷二心,今其遠遁萬里,士卒疲敝,正是用兵之時。」
他提出一個大膽的計劃,就地徵調西域屬國兵馬,聯合漢朝屯田吏士,趁匈奴立足未穩發動奇襲。
甘延壽聞言大驚:「不發虎符而擅調大軍,這是滅族之罪!」
陳湯卻凝視著跳動的燈火,一字一句道:
「郅支單于視漢如無物,西域各國離心離德,若等朝廷往復辯論,恐西域已非漢有。」
兩個漢朝使臣相對無言,遠方的地平線上,康居國的燈火如鬼火般明滅不定,那裡有囂張的匈奴單于,有被辱殺的漢使亡魂,更有一個帝國搖搖欲墜的尊嚴。
矯詔出兵
甘延壽病倒的消息傳來時,陳湯正在擦拭佩劍。
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