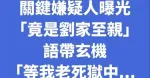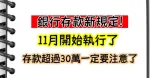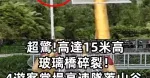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西漢名將一生只打一仗,換中國三百年無人敢犯,一句名言流傳至今

3/3
他知道不能再等了,每拖延一刻,郅支單于的勢力就壯大一分,西域各國觀望的耐心就減少一分。
這個出身寒微的將領做出了一個足以誅滅九族的決定:假傳聖旨,調兵出征。
當他的手握住那方沉甸甸的都護印信時,冰涼的觸感讓他想起詔獄裡的鐐銬,但這一次,他甘願為自己套上命運的枷鎖。
矯詔的過程出乎意料地順利。
各城郭國早就苦於匈奴壓榨,見到蓋有漢印的文書,幾乎沒有任何懷疑。
烏孫、大宛等國紛紛出兵,車師屯田的漢軍士卒更是聞訊即動。
短短十餘日,四萬大軍已然集結完畢,戰馬嘶鳴,旌旗蔽日。
當甘延壽拖著病體衝出營帳時,看到的是整裝待發的浩蕩軍隊。
他怒不可遏地抓住陳湯的衣襟:「你可知這是滅門之罪!」
陳湯平靜地推開他的手:
「一切罪責我自承擔,但若放過此次戰機,西域將永淪胡塵,你我都將成為千古罪人。」
大軍如鋼鐵洪流般湧向康居。
行軍途中,陳湯將軍隊分為六校,三校取道蔥嶺直插大宛斷敵後路,三校隨都護正面推進。
時值深秋,漠北寒風如刀,漢軍士卒手腳凍裂,卻無一人退縮。
因為他們看到那位文官出身的副校尉始終走在隊伍最前列。
在距離康居邊境三十里處,陳湯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。
他秘密召見了康居貴胄開牟,這個被郅支單于奪去草場的貴族,在聽完漢使的承諾後,毫不猶豫地答應作為嚮導。
當夜,開牟帶著陳湯的親筆信潛入康居各部,很快就有消息傳來,郅支單于的暴政早已天怒人怨,許多部落願意暗中相助。
決戰在單于城下展開,匈奴騎兵在城下來回奔馳,發出挑釁的呼嘯。
陳湯卻不為所動,冷靜地指揮部隊構築工事。
次日黎明,單于果然按捺不住,派百餘騎衝出城門直撲漢營,陳湯早有準備,弩箭如暴雨般傾瀉,匈奴騎兵尚未接近陣線就已人仰馬翻。
真正的考驗發生在第三天深夜。
康居國的一萬援軍突然出現在漢軍背後,與城內守軍形成夾擊之勢。
陳湯拔出長劍,親自躍上戰車:「今日有進無退!」
他命令弓弩手組成三道防線阻擊援軍,同時集中精銳猛攻城門。
戰鬥持續了整整一夜,直至黎明時分,最前方的漢軍士兵突然發出震天動地的歡呼,城門破了!
陳湯一馬當先沖入城內,巷戰異常慘烈,匈奴人憑藉熟悉的地形負隅頑抗。
在混戰中,陳湯突然瞥見城樓上那個身披金甲的身影。
郅支單于正聲嘶力竭地指揮作戰,完全沒注意到一支弩箭正對準他的面門。
弓弦響處,單于慘叫一聲捂住血流如注的鼻子,隨即被蜂擁而上的漢軍淹沒。
當軍侯杜勛割下郅支單于的首級時,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梟雄,眼睛還圓睜著難以置信的神情。
陳湯站在單于城的廢墟上,望著繳獲的漢使節杖和帛書。
方的地平線上,倖存的康居騎兵正在倉皇逃竄,而更遠處,絲綢之路的駝鈴仿佛又重新響了起來。
名垂青史
凱旋的號角聲響徹玉門關,陳湯和甘延壽押著俘虜、帶著郅支單于的首級班師回朝。
但迎接他們的,卻是御史大夫匡衡冰冷的彈劾奏章。
「矯詔興兵,大逆不道」八個字如利劍般懸在未央宮大殿之上。
漢元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兩難,功高莫過於救社稷,罪極莫過於違皇權,兩者皆有,如何收場?
最終,宗正劉向的一席話打動了皇帝:
「陳湯之誅郅支,揚威域外,雪恥國讎,雖《春秋》之義不過如此。」
漢元帝終於下旨封賞,長安百姓爭相傳頌「矯詔將軍」的傳奇。
但當陳湯在慶功宴上舉起金樽時,他不會想到,這竟是他人生中最後一個輝煌時刻。
成帝繼位後,朝局變幻,匡衡等大臣舊事重提,此後數年,他就像一枚被隨手擺弄的棋子,時而復起為射聲校尉,時而被貶為庶民徙邊敦煌。
最諷刺的是,當西域再度告急時,朝廷又不得不啟用這個「有罪之臣」。
晚年的陳湯蝸居在長安陋巷,舊部杜勛前來探望,言語之間,仿佛又帶回二十年前那個改變歷史的時刻。
當他將郅支單于的首級獻於御前時,那聲響徹雲霄的誓言:
「明犯強漢者,雖遠必誅!」
這個出身寒微的將領做出了一個足以誅滅九族的決定:假傳聖旨,調兵出征。
當他的手握住那方沉甸甸的都護印信時,冰涼的觸感讓他想起詔獄裡的鐐銬,但這一次,他甘願為自己套上命運的枷鎖。
矯詔的過程出乎意料地順利。
各城郭國早就苦於匈奴壓榨,見到蓋有漢印的文書,幾乎沒有任何懷疑。
烏孫、大宛等國紛紛出兵,車師屯田的漢軍士卒更是聞訊即動。
短短十餘日,四萬大軍已然集結完畢,戰馬嘶鳴,旌旗蔽日。
當甘延壽拖著病體衝出營帳時,看到的是整裝待發的浩蕩軍隊。
他怒不可遏地抓住陳湯的衣襟:「你可知這是滅門之罪!」
陳湯平靜地推開他的手:
「一切罪責我自承擔,但若放過此次戰機,西域將永淪胡塵,你我都將成為千古罪人。」
大軍如鋼鐵洪流般湧向康居。
行軍途中,陳湯將軍隊分為六校,三校取道蔥嶺直插大宛斷敵後路,三校隨都護正面推進。
時值深秋,漠北寒風如刀,漢軍士卒手腳凍裂,卻無一人退縮。
因為他們看到那位文官出身的副校尉始終走在隊伍最前列。
在距離康居邊境三十里處,陳湯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。
他秘密召見了康居貴胄開牟,這個被郅支單于奪去草場的貴族,在聽完漢使的承諾後,毫不猶豫地答應作為嚮導。
當夜,開牟帶著陳湯的親筆信潛入康居各部,很快就有消息傳來,郅支單于的暴政早已天怒人怨,許多部落願意暗中相助。
決戰在單于城下展開,匈奴騎兵在城下來回奔馳,發出挑釁的呼嘯。
陳湯卻不為所動,冷靜地指揮部隊構築工事。
次日黎明,單于果然按捺不住,派百餘騎衝出城門直撲漢營,陳湯早有準備,弩箭如暴雨般傾瀉,匈奴騎兵尚未接近陣線就已人仰馬翻。
真正的考驗發生在第三天深夜。
康居國的一萬援軍突然出現在漢軍背後,與城內守軍形成夾擊之勢。
陳湯拔出長劍,親自躍上戰車:「今日有進無退!」
他命令弓弩手組成三道防線阻擊援軍,同時集中精銳猛攻城門。
戰鬥持續了整整一夜,直至黎明時分,最前方的漢軍士兵突然發出震天動地的歡呼,城門破了!
陳湯一馬當先沖入城內,巷戰異常慘烈,匈奴人憑藉熟悉的地形負隅頑抗。
在混戰中,陳湯突然瞥見城樓上那個身披金甲的身影。
郅支單于正聲嘶力竭地指揮作戰,完全沒注意到一支弩箭正對準他的面門。
弓弦響處,單于慘叫一聲捂住血流如注的鼻子,隨即被蜂擁而上的漢軍淹沒。
當軍侯杜勛割下郅支單于的首級時,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梟雄,眼睛還圓睜著難以置信的神情。
陳湯站在單于城的廢墟上,望著繳獲的漢使節杖和帛書。
方的地平線上,倖存的康居騎兵正在倉皇逃竄,而更遠處,絲綢之路的駝鈴仿佛又重新響了起來。
名垂青史
凱旋的號角聲響徹玉門關,陳湯和甘延壽押著俘虜、帶著郅支單于的首級班師回朝。
但迎接他們的,卻是御史大夫匡衡冰冷的彈劾奏章。
「矯詔興兵,大逆不道」八個字如利劍般懸在未央宮大殿之上。
漢元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兩難,功高莫過於救社稷,罪極莫過於違皇權,兩者皆有,如何收場?
最終,宗正劉向的一席話打動了皇帝:
「陳湯之誅郅支,揚威域外,雪恥國讎,雖《春秋》之義不過如此。」
漢元帝終於下旨封賞,長安百姓爭相傳頌「矯詔將軍」的傳奇。
但當陳湯在慶功宴上舉起金樽時,他不會想到,這竟是他人生中最後一個輝煌時刻。
成帝繼位後,朝局變幻,匡衡等大臣舊事重提,此後數年,他就像一枚被隨手擺弄的棋子,時而復起為射聲校尉,時而被貶為庶民徙邊敦煌。
最諷刺的是,當西域再度告急時,朝廷又不得不啟用這個「有罪之臣」。
晚年的陳湯蝸居在長安陋巷,舊部杜勛前來探望,言語之間,仿佛又帶回二十年前那個改變歷史的時刻。
當他將郅支單于的首級獻於御前時,那聲響徹雲霄的誓言:
「明犯強漢者,雖遠必誅!」
 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